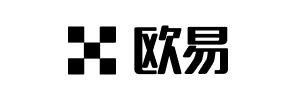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钩挂三方来闯荡:
老蒋、鬼子、青洪帮!”
邱县是冀鲁豫大平原上的小县,原属山东,今属河北。
按理说,边界地区应该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但这里不是湘赣边,没有高山深林。尽管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激烈,却由于夹在冀鲁两省军阀之间,稍有风吹草动,不是宋哲元的马队来“剿”,就是韩复榘的侦探来抓,我党地下活动很难开展。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土崩瓦解。鬼子还没来,县长王廷延就跑了,邱县进入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

河北省主席 宋哲元
秦失其鹿,县城里的地主、士绅、恶霸、兵痞自然要共逐之,他们乘机搞了个半政权性质的“支应局”。说白了就是“维持会”,谁来都“支应”,只要能“维持”老爷的“体面”,随时可以出卖群众的利益,哪怕是卖给日本人。什么民族气节,哪叫国家利益,只要老爷还是老爷,下人仍是下人,卖给谁不是卖?
11月15日,日军侵占邱县,为报复二十九军的抵抗,展开疯狂的大屠杀。半天之内,即残杀我同胞808人。
兽兵借口搜查“溃军”,进入街巷,一家不隔,逢人就砍,见人就杀。东街王小子是“九宫道”徒,听说日军进城,赶紧跪在屋里烧香祷告。九宫道是封建迷信的反动会道门,跟日寇汉奸早有勾结,宣扬日本入侵是中国劫数难逃,要求教众“躺平”,不要反抗,顺其自然。鬼子可不跟你讲道理,破门而入,开枪就把王小子给杀了。西街石富春家,先打死石富春,老婆正怀有八九个月身孕,鬼子一刺刀下去,挑开肚子,把血淋淋的婴儿挑出来,最后又残忍地挑杀了在炕上大哭的三个孩子。城外东屯李成林,被鬼子砍了头,挂在树上示众。仅东西南街,被日军杀绝户的就有14家。

山东省主席 韩复榘
从此,邱县沦陷,邱县人民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
为了求生存,各种打着“抗日”旗号的民间武装蜂起,各路“司令”多如牛毛,谁来都向群众派粮派款。说他们是抗日武装,不如说是“土匪”更合适。特别是土豪劣绅所掌握的民团武装,也跟土匪相勾结,助纣为虐,危害更甚。当时的邱县,县城周围的匪团,就有26股之多,号称“二十六路反王”。日伪加上土匪,到处烧杀抢掠,社会极其混乱,民不聊生,暗无天日。
群众无依无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他们的思想和要求,就是极端仇恨日寇,极端不满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强烈要求抗日,消灭匪伪。
马固小学教员王屏,忧心忡忡,18岁的他,别看年轻,已经是位老资格的地下党。16岁入党,即被推为邱县第一个党支部的支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白色恐怖下,虽然与上级失去联系,但王屏他们初心不改,坚持抗日宣传,秘密发展组织。
如今,国民党的县长跑了,国民党员虽然全县也有一百多人,但多数都是土豪劣绅和官僚,不仅完全代表地主利益,直接压迫工农群众,而且毫无抗日斗志。是时候,共产党员要站出来,组织群众,搞武器,拉起武装,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保卫家乡,保卫人民。
王屏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武装,就寸步难行!”
问题是人和枪,从哪里来呢?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本地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也只搞到八九枝枪,组织了个十几人的游击队。跟上级组织联系上之后,又配合直南临时特委,争取土匪李景隆部二百多人,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第一师。
这个李景隆,出身小地主家庭,收入有限,却不事经营,也不识字,整天吃喝嫖赌,抽大烟,挥金如土,好交朋友,整天“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抗战爆发后,拉起民团武装,实际上就是土匪。不过奸淫掳掠,都到广宗、威县和南宫一带,不在本地作恶,所以在邱县没什么民愤。我们想改编他,使之成为抗日武装。
但我们的纪律,李景隆受不了,没多久借口到邢台敌占区,要说服汉奸高德林反正抗日,带着几个护兵跑了。结果,他也下水当汉奸,官拜“皇协剿‘匪’第二军宪兵大队”大队长。后来,我们几次做思想工作,希望他反正。李景隆只说现在人太少,等力量壮大了不迟。实际上,满脑子吃喝玩乐,那管什么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在敌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他也根本不相信八路军能够打走日本。加上自身贪图享受,不能吃苦的弱点,最终日本人忍无可忍把李景隆踢了,毕竟养汉奸不是办慈善!
1938年5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到达冀南。首战威县,打跑了盘踞县城的日军,接着乘胜向漳河以南和卫河两岸进军。
八路军的胜利,让冀鲁豫人民看到了希望,也让地方游杂武装中的一些人,开始选择正确的方向站队。随后,一支番号“冀南抗日游击第二师”的队伍,驻扎到了邱县。该师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认真执行“三六纪律、八项注意”,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受到了邱县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但你可能万万想不到,这支队伍的“老大”李侍曾,此前不但是个标准“草头王”,甚至还下水当过一段时间的汉奸。
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促成李侍曾的转变,促成了这支队伍的转变呢?
光绪十八年(1892),李侍曾生于本县贺钊镇西庄(今河北威县侍曾村)一个地主家庭。五岁时,家里遭了土匪,再加上被恶霸缠上打官司,最终破产。他虽聪慧好学,祖上出过秀才,也只能少而失学,11岁就开始打零工,农忙给富户家扛活,冬闲时做小生意,卖花生、梨膏糖。长大后,还当过牛贩子,四处闯荡。
1920年,华北大旱,灾害严重,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为谋生计,李侍曾托关系,到地主武装里,补了个民团兵。因为会来事,善交际,又能打能冲,得“贵人”相助,一路升迁。作过邱县公安局武装大队的骑兵班长、中队长,邱县、高密县公安局长。还拜当地青帮大佬为师,成为“念(廿)四”学字辈大佬,又开了香堂,当上“老头子”,在周围几个县收了上千的徒弟。
有了这些资本,李侍曾也发达起来,置房置地,娶了老婆,还纳了小妾。
抗战之初,地方秩序动荡,李景隆率土匪,四处洗劫,也曾打过贺钊的主意。因为是李侍曾的徒弟,不敢太“造次”,却也讹走了三千块“慰劳费”。本地乡绅赶紧请李侍曾出山,以“保乡保家”为名,成立了“壮丁队”。李侍曾名气太大了,官私两面,黑白两道,都得给面子,于是邱县、威县、临清、冠县和清河的民团,纷纷投奔,又收缴了不少国民党散兵的马匹枪支。壮丁队发展到三千多人枪,还有一百多匹战马组成的马队。
大地主的目的,说是“保乡保家”,实际上谁能保证其阶级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就跟谁干。在当时,那就是日本人。不久,在豪绅包围和日寇胁迫下,“壮丁队”被日寇收编为“清水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二团”,李侍曾为团长。
汉奸可不是啥好名声,原来李侍曾在当地人称“赛孟尝”,如今骂大街的可不少。长期跟随他的不少旧部,还有亲朋好友,基于义愤,对他规劝指责,进而相继离去,大批社会渣滓和土豪劣绅则乘机涌来。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也派人拉拢,许以高官厚禄,说你完全可以“两头吃”,只要打八路就行。
何去何从,犹豫徘徊,李侍曾陷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
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先后派出几路人马,试图挽救李侍曾,其中就包括李侍曾的族侄李子方。
李侍曾无子,唯有一个养女,李子方从小就跟李侍曾亲近,又是师范生、小学教员,被认为是李家后生中最优秀的一个,所谓“吾家千里驹”。自然深得重用,留在身边,任命为警卫连长兼随从秘书。
只是李侍曾不知道,李子方同志,此时已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了。
通过接触,李子方发现:李侍曾对被日寇收编当汉奸,非常不甘心,对地主豪绅为了自己利益,设局让李侍曾钻,骂名别人顶,好处他们占,相当不满意。此外,虽然是旧官吏出身,但李侍曾跟共产党无冤无仇,甚至还曾掩护过他佩服人格品行的共产党员脱逃。跟国民党没啥联系,基本是看不起、瞧不上的态度。其人性情刚直,有爱国保家之心,这些都是能够被我争取,反正过来的有利条件。
有有利条件,就有不利条件:作为地方实力派,旧军人出身,李侍曾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有多年的混事经验,江湖积习较重,部队成分很杂。对共产党基本没啥了解,反而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误解,知道红军能打仗,把毛泽东、朱德等同“梁山好汉”来敬仰。
但李侍曾也严重怀疑我们,甚至整个中国,能不能打得过日本?毕竟日本人要啥有啥,飞机坦克,国民党、中央军都扛不住,你们几条破枪,凭啥敢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撵出中国”?对于中国抗战前途,以及中华民族未来的解放和发展前途,更是茫然无知,想都没想过了。
这就决了,即便当下,我们能说服李侍曾,接受我党我军的教育和改编,未来他和他的这支队伍,能跟我们走多远,能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会不会出现反复,绝不是一帆风顺,手拿把掐的事情。
李子方同志没有公开身份,所以李侍曾暂时还没有怀疑到,前者和“八路说客”,其实是一头儿的。八路军派来联络的同志,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冷遇。尽管好吃好喝好招待,走的时候还送路费,但李侍曾借口“军务繁忙”,拒不接见。来得多了,也只是让李子方去“对付”。
当然,国民党来人,无论是打着中央、地方旗号,还是党政军哪方面的,李侍曾也是这态度。地方豪绅、汉奸和青帮,有的是他的老熟人,如今也不见面,包括书信往来,一概由李子方办理接待。
这也有个好处,屏蔽了各种有害和无效信息,方便李子方同志持续做李侍曾的思想工作。
随着冀南抗战形势的迅猛发展,八路军连战连捷,名头越来越亮,李侍曾的心理天平,逐渐向左倾斜了,不断向李子方,打听共产党、八路军方面的情况,询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共产党共产共妻是真的吗?
我有两个老婆,怎么办?会不会被‘共’一个,要不你先把你‘小大娘’送走,省得到时候麻烦。
共产党会相信我吗?把我当成汉奸怎么办?
听说共产党都是念书识字的人,是吗?你在共产党没有?
你见过八路军吗?八路军是不是‘朱、毛’的红军?
国民党那么多军队都跑了,八路军能打赢日本吗?
……
这些问题,李子方都尽量回答,尽量通俗易懂,但李侍曾却反复提出这类问题,不断求证,显然他的思想松动了,不过仍有相当的顾虑和怀疑。毕竟军队是他的命根子,搞不好鸡飞蛋打,我为鱼肉,人为刀殂的时候,可就回不了头了!
思来想去,李侍曾决定先找青帮的师兄弟,盘踞在香城固一带,同属伪“清水部队警备一旅”,大土匪头子王来贤聊聊。这一去就是七八天,回来的时候,臊眉耷眼,骂骂咧咧。本来想找王来贤倾诉衷肠:怕背上汉奸的恶名,将来愧对祖宗;又怕共产党不能相容,投奔过去,遭了暗算。想找王来贤,给他当个保险,不料王来贤不仗义,看李侍曾只带了几个护兵来的,就想趁机搞掉李侍曾,吞了他的人马。
据说最后,要不是本地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出面,李侍曾就得折在王来贤手里。
不过,找了王来贤,李侍曾的政治态度,却豁然开朗,告诉李子方:“以后那边(国民党的河北民军)来的人,不要理他们;南边(土匪汉奸王来贤)来了人,扣起来!”
没多久,李侍曾处决了一个姓徐的连长。此人原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排长,部队南撤的时候,带着手底下的人哗变。又纠集了几十个逃兵,在当地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因为装备好,战斗技术过硬,被李侍曾收编,当上了连长。但此人恶习不改,李侍曾原本还记得“人才难得”,这次也想明白了,早晚是个祸害,等成了“小王来贤”,可就麻烦了。
从处决徐连长开始,李侍曾陆续整顿纪律,有些人觉得他“变”了。
1938年1月,一夜之间,附近来村子来了支“马队”——八路军东进纵队骑兵连。让人啧啧惊奇的是,他们竟然神兵天降,几乎全无声息,就跑了上百里夜路。
到了目的地,顾不得休息,大多数人就深入群众,有的访贫问苦,有的给群众打扫卫生、修缮房屋,还有的在街上刷写抗日标语,向群众宣讲八路军的纪律和抗日政策,教村里的孩子识字、唱歌。战马更是管得规规矩矩,为了不让啃群众的树木,甚至用被褥裹住树干。
群众慨叹:“这样好的队伍,可是头回见!”
李侍曾听说后,赶紧带着李子方去观摩。他也是老行伍了,对八路军艰苦的作风,严明的纪律,对群众亲如一家的态度,还有别家军队完全见不到的新鲜做法,赞叹不已。这时候,李侍曾也不怕八路要“吃”他了。
回来的路上,还跟李子方说,你注意到了吗,这些八路都是“蛮子口音”,江西红军,江西红军啊!
1938年元月一天晚上,由任县邢家湾进驻威县鱼堤。真如神兵天降,人心沸腾起来,侍曾马上要他族侄代表他前去欢迎和慰劳。他详细询其实我们知道,八路军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改编。这些南方口音的同志,不是来自鄂豫皖,就是四川人。不过,当时不像现在,多数北方人根本搞不清南方口音的显著差异。
经过几个月的复杂斗争和紧张工作,李侍曾最终下定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抗日救国的道路,毅然率所部两千余人,宣布反正,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
随着社会渣滓被淘汰,一批青年学生和共产党员输入部队,部队又随之扩大。但部队成份仍很复杂,一部分权力和重要位置,还把持在国民党分子和豪绅手中。
完成改编不久,独二师参加了威县攻城战斗。
尽管李侍曾言语恳请,多次争取要参加主攻,但八路军领导还是安排独二师打埋伏,只抽调警卫连的7名本地战士当向导。
这里请大家注意:李侍曾的“恳切”,其实是迫不得已。毕竟旧军队往往这个时候,习惯于借刀杀人,慷他人之慨,让新编部队送死,正所谓“打死外敌除外患,打死杂牌平内乱。”老李见得多了,可八路军把“送死”的任务,留给自己的主力部队,干部和党员,嗷嗷叫地请战。欣慰之余,他也有点汗颜:打鬼子杀汉奸,本地人咋能甘居外地人后呢?
说到这里,冀鲁豫人民真是可爱,他们敦厚勇敢,无所畏惧,自义和团运动以来,就有深厚而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听说八路军要打威县,当地不少农民,主动请缨,要求带路,甚至参与战斗。有位五十多岁的老乡,扛着一把磨得锃明瓦亮的大砍刀,自报奋勇,要随军爬城。
5月10日凌晨,威县战斗打响。
一开始进展很顺利,但关键时刻,原来答应跟我们里应外合的,伪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和梦九,突然反水。死心塌地给鬼子效命,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我入城的114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这其中主要是六八九团的同志,也包括李侍曾警卫连的三位战士和两位农民。
那位农民英雄,第一个从城东北角爬云梯登城,也壮烈牺牲在攻城战斗中。名字都没有留下,只知道他是威县七里苏人。但是“七里苏”在威县哪里?我在今天的地图上,没有找到,心里满是愧疚。
威县战斗后,李侍曾憋着一口气,对李子方说:“我再也不想‘独立’了,我想当八路!”
由此,“独二师”整编为“八路军冀鲁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李侍曾还主动提出,这支“新八路”,也要像“老八路”一样,设立政治机关,“请给我派个政委吧!”
可是旧军人向革命军人的转变,哪有那么容易?好像摁一下按钮,灯就亮了,其间是需要做大量且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又:我们河南有句老话,叫:“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咋跑?”
曾几何时,我们的影视剧,表现我军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者,那实在是一言难尽(不能一棒子打死,也有好的,比如电视剧《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政工人员应有刻苦任劳、牺牲奋斗之精神,待人待物要和蔼,不可有浪漫之行为。要过最苦之生活,对与士卒同甘共苦这句话要兑现。各级政工人员过去过于重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而忽略士兵政治训练,结果不但不能组织与训练民众,而士兵亦不知训练为何物,致军纪荡然。”
这段话,是张发奎在1939年日记中的慨叹,张发奎是见证过国共两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四军当年为啥能叫“铁军”,与共产党员在四军中的特殊表现,以及我军在四军中所做的政治工作,是离不开。但是大家请注意,那个阶段,国民革命军中我党同志搞的政治工作,还是不成熟的1.0版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这些年,写了多少这方面的东西,就知道差距了。
所以说,国民党里面不是没有明白人,为啥做不到呢?即便是中央军和曾经非常重视政治工作,有政工传统的张发奎部队,也做不好呢?
说到底,还是军队的阶级属性。不讲清楚这个,什么都是扯淡!
2025年6月28日19:27于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