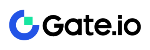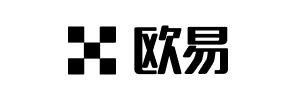编者按
“神权政府”的标签,长久以来遮蔽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复杂的政治现实。伊朗的韧性并非源于僵化的中世纪神权,而是植根于法团主义社会结构与受社会力量制约的裙带资本主义经济的共生体中。遍布社会末梢的“巴斯基”组织,远超准军事范畴,是集福利分配、社会控制、政治动员于一体的国家触手。它为中下阶层提供稀缺的上升通道与社会保障(如教育配额、公职机会),织就民众与统治集团间现实而微妙的利益纽带。
与此同时,经济私有化浪潮虽引发广泛民怨,却并未导向自由市场,反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宗教基金会(Bonyads)及巴斯基关联企业等特权集团主导,形成服务于统治核心的裙带网络。然而,法团主义的土壤也催生了自下而上的制约——民众通过社会组织(如工会、巴斯基)部分阻止了国有资产完全私有化,使其滞留在“集体”控制的模糊地带。
本文有力驳斥了将伊朗比附为“21世纪的大清”的肤浅论调,指出其社会整合与畸形资本形态恰是当代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变体。理解这种内生、扎根社会的统治逻辑——而非沉溺于妖魔化或外部颠覆的幻想——才是关键。推翻神权统治需直面其物质根基。在此框架下,对以色列侵略的谴责与对伊朗统治集团的批判,具有辩证的统一性。

伊斯兰共和国:传统与现代之间?
前言
以色列与伊朗神权政府的冲突已经持续了数年——在这一进程当中,以色列不断地通过运用其高超的技术手段与情报系统而打击伊朗神权政府的枢纽,但是——每当人们认为神权政府会为此而崩溃之时,它都继续存活了下来。
尽管人们习惯性地将伊朗称为‘神权政府’——但是,正如其一次又一次的‘幸存’所表明的,这种称呼是误导性的:决定伊斯兰共和国的命运的并非一两个‘超凡领袖’,而是其整个社会。伊朗政府是威权的,但并非权力高度集中,是与人民的利益相敌对的,但并非不能得到人民的合法性认同。认为伊朗政权可以仅仅通过消灭其‘领导’而被战胜的人误以为它停留在中世纪,这正是因为他们只关注政治的表象,而根本上无视了伊朗的社会与经济现实。
必须强调,本文的立场是左翼的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为此,本文绝不是为伊朗的政权进行任何意义上的辩护。但是,为了战胜它,必须首先理解它,而不是停留在刻板的,荒诞不经的妖魔化叙事当中,误以为只要礼萨巴列维——这个可耻的亡国之君的后裔,躲在哪个不知道在何处的,供他花天酒地的场所里胡乱的嘟囔几声,伊朗人民就会揭竿而起。
如何界定伊朗的社会性质?本文不打算在这里重复有关于伊朗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究竟如何的讨论——这种讨论的终点常常将我们引向一个庸俗的比附:伊朗是21世纪的大清——通过洋务运动,它在‘器物’上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在社会组织上,特别是在政治上,它还远远落后于现代。如果说究竟是什么给了部分人将伊朗解读为‘阿塞拜疆人小族临大国’这种荒唐的说法以灵感,那么大陆互联网上长期将伊朗的社会与政治体制视为‘前现代’,进而比附为大清朝的说法显然脱不了干系。
本文意在挑战这样一点,并提出这样一个在近年来才逐渐被人关注的论断:伊朗的社会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法团主义,而在经济上则不出意外的是受到自下而上制约的裙带资本主义。它意味着,首先,伊朗的社会并非能够被简单地概括为自上而下的‘独裁’,仿佛伊朗的普通民众陷入了一种彻底原子化的被动之中,而是在双方的积极的(这里的‘积极’甚至不完全是讽刺的)合力下运行;其次,伊朗不是简单的前资本主义‘教士集团’掌舵,它的首要目标不是尽快‘实现资本主义’而完成‘历史进步’,相反,在‘解放’伊朗的进程当中,被解放的主体将会是‘自由的’资本。
1
Part.1
巴斯基(Basij)与伊朗式的法团主义
本文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伊朗的巴斯基‘民兵’制度——在一般的叙述当中,它被称为‘民兵’组织或‘准军事’组织——这正是我们把‘民兵’这个词打上引号的原因。通俗的叙事是,伊朗的‘教士集团’十分恐惧世俗力量,包括政府,所以他们设置了独立的武装,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其民间的从属者,巴斯基民兵,主要用作内卫部队,负责镇压反对派。
这种说法的困境在于,它无法解释在所谓的‘巴斯基’力量,即‘抵抗动员’力量当中,广泛存在着非军事职能的单位,例如‘工人巴斯基’(Sazman-eh Basij-eh Kargari),行会巴斯基(Sazman-eh Basij-eh Asnaf),甚至学生与教师巴斯基(王国兵 2019;Mazaheri 2020)。所有的这些均得到了实地考察的认可,并受到伊朗官方的承认(iranwire.com)。尽管有其军事起源,但是这些部门却日益占据着巴斯基的核心,并不断壮大——这根本不能用‘准军事组织’的理论来加以解释。
根据Mazaheri(2020)的说法,
工人巴斯基有超过100万名成员。伊朗法律规定,凡拥有超过30名雇员的地方,必须要成立巴斯基的‘基地’,从而加强了工人间的团结,交流和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为此(在我看来),巴斯基为伊朗的工人阶级赋予了力量。
来自同样遥远的东方古国的读者不会不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正如Mazaheri所试图指出的,巴斯基实质上是党委与工会的混合体。但是,这显然不是什么‘前现代’体制。
究其本质而言,巴斯基实际上是伊朗政府伸向整个市民社会的触手,是渗透每一个个体的个人生活的工具。写道:
巴斯基的基本单位是“抵抗基地”,这些出现在每个社会领域:清真寺,社区,工厂,办公室,学校——任何人们聚集的任何地方。毫无疑问,这是巴斯基最重要的一层,因为这是人们互动的地方;这是社会的根源。该国可能有 60,000-80,000 个这样的基地(记住,伊朗一共也只有 72,000 座清真寺),其中约 75% 位于城市地区,因为伊朗是一个 75% 都是城市国家....这些团体中的每一个都有两个抵抗小组,每个小组至少有 4-5 人。每个巴斯基基地大约有几十到 100 多名成员,都在意识形态上合作。
为此,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伊朗正处在一种中世纪晚期的‘平行发展’当中,仿佛一边是‘日益觉醒的市民’,另一边则是昏聩老迈的教士。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二者并不是平行的两个‘伊朗’(这又是互联网上通过‘我认识的伊朗人’所制造的一个神话),而是通过无数像巴斯基这样的组织被缠绕在一起的一个伊朗。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伊朗的市民并不欢迎以色列的侵略,也没有从内部发起‘革命’。
但是,伊朗的社会与‘神权政府’的关系并非简单地被支配与支配者的关系。法团主义不可与彻底的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社会相混淆,后者的特点是民众的被动与无力,被彻底打散和肢解,与其相反,法团主义的特定不在于直接迫使个体面对国家权力,而在于通过社会团体的中介控制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并没有被摧毁,而只是被绑架,社会团体仍然可能有其自主性与自由。陶里亚蒂(1973)在《法西斯主义八讲》(Lectures on Fascism)当中谈到,尽管国家法西斯党已经控制了工会,但是,对于残存的,仍未暴露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仍然需要打入这些工会当中进行活动——在那里法西斯主义者仍然在试图与社会主义者进行争夺。
让我们看看 1925 年 FIAT 的金属工人的罢工。不要忘记,是法西斯主义者最早提出了罢工。他们由此赢得了数千名工人加入他们。他们紧接着还想通过提高工资的承诺收买更多人。但是这一次他们失败了。为什么?因为都林的工会形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集团,他们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你想要涨工资就要斗争,但是你们法西斯主义者敢于斗争吗?你们不是说要罢工吗?那好,我们罢工。罢工的主动权到了 FIOM 手中。(64)
伊朗的情况正是如此。在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的劳工组织逐渐形成,并被作为‘革命’的一部分而继承了下来。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政府加强了对于基层的劳工组织的控制,清洗了隶属于自由主义和激进左翼的管理层,但并没有摧毁它们,特别是,保留了各地的工人委员会,而只是加以“伊斯兰主义”的限制(Hossein Kamali在1980年代宣称。‘伊斯兰工人委员会是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继承者’,他隶属于伊斯兰共和党当中被称为‘劳工派’的派别)。正如Kalb(2024)指出的,战争也同时迫使精英意识到他们需要劳工与社会大众的支持,进而加强了对于后者的统合与‘统战’:在政治斗争当中,不是彻底的精英主义者,而是法团主义者取得了胜利。特别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司法部门在其中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它们支持工厂委员会的观念,并发起了‘首次全国伊斯兰协会工厂大会’(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factory Islamic associations)。伊朗也逐渐形成了以‘工人之家’(Workers’ house,khaneh-ye kârgar)为核心的全国性工会体制。工人之家积极地与商业和政治精英合作,平衡各方利益。伊朗当局对于它的表现相当满意,但是工人和市民也是一样——甚至,在伊朗199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它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主导作用。
巴斯基是另一个多方‘共谋’的场所。Mazaheri认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化团体’,承担着财富再分配和福利保障的功能。这一点无疑体现在它在伊朗的‘底层人’当中的受欢迎的程度之上:
Golkar(一位反对伊朗政府的研究者)自己通过大量关于伊朗国内巴斯基人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明确表示,巴斯基人主要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如果他不这么说,伊朗人倒会感到震惊,因为这只是证实了一个常识:‘关于巴斯基部队的社会起源,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来自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其他地方 Golkar 又写到:“事实上,伊朗的‘被压迫者’似乎是巴斯基招募的主要来源。”
这是因为,巴斯基在内部为其成员保留了大量的福利与社会流动渠道。‘40%的本科生与20%的研究生名额是保留给巴斯基成员的’,对于妇女,巴斯基是唯一能够为她们提供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特别是政府和公共部门工作的机会的渠道。
同样地,像工会一样,巴斯基也保留了一定的社会独立性。Mazaheri 称其为‘非政治的’(尽管它显然不是):
1996 年,巴斯基使伊斯兰共和党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的伊朗建设公仆党的则位居第二。这是巴斯基第一次公开参与政治。坐在伊朗政府等级制度中巴斯基之上的革命卫队和最高领袖对此很满意。但仅仅一年后的 1997 年,就有 73% 的巴斯基成员投票支持改革派哈塔米担任总统。巴斯基随后“恢复了组织”,帮助保守派内贾德赢得两个任期。但随后他们又改为帮助改革派鲁哈尼在 2013 年和 2017 年赢得了第一轮的彻底胜利。
显然,巴斯基绝非是任何意义上的“极权体制”的一部分,但是,它这种偶尔的“动摇”并不会使其受到统治者的怀疑,因为它总体上仍然是受控的。在这一进程当中,统治者与人民达成了平衡,甚至局部的融合。
2
Part.2
伊朗的裙带资本主义,以及它如何在事实上收买人民
但是,伊朗的社会整合也带来了同样严重的问题——这种社会整合是不完全和有条件的,它的目的是服务一个超然于社会之上的阶级。为此,伊朗的法团主义并不是通过一视同仁的方式而进行的,而是力图‘收买’一部分人,调和其与统治者的关系,变成拥护统治的‘基本盘’。在这一进程当中,它就能够以‘人民利益’的旗号而大肆地推行裙带资本主义。
之所以称伊朗为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在国内与国外的两个方面都极度依赖于市场和价值生产:在对外方面,伊朗经济高度依赖于出口,而在国内,伊朗虽然一度有过极高的国有化率,但是在 2005 年之后则进入了快速的私有化进程当中,计划将价值 1300 亿美元的主要国有企业上市,其股票的 80% 出售给‘私营部门’,并将其中的 10% 分配给外国投资者。同时逐步地放开价格管制,减少补贴,包括对日常的民众生活用品的补贴。
(https://www.bicc.org.uk/co-privatisation.html)
但是,让我们切勿轻率地认为这主要是得到‘改革派’的欢迎,恰恰相反——由于伊朗政府的私有化大幅减少补贴,采用紧缩政策,它招致了伊朗人民的极度不满。在哈塔米(改革派总统)时期,改革进程举步维艰,而到了内贾德(保守派总统)上台之后,却推出了史无前例的‘补贴改革’——全部日用品价格均大幅上涨。尽管如此,内贾德最初的举动仍然十分谨慎,没有推动重工业,交通,电信和银行的私有化,直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人在2007年发出‘呼吁’(韩建伟 2024)。而在今天,仍然能不时看到保守派的相关人物发出类似的‘呼吁’。在2025年2月24日,Iran International 发布了一篇报道,在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 Mohammad Bagheri 呼吁实施更加激进和彻底的私有化,这位将军说到:‘拯救国家的模式是求助于人民。如果我们想解决经济问题,解决方案是求助于私营部门,必须将工作委托给人民’。
一些来自于东方的观众常常将本国的历史投射到异域——他们误以为伊朗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在经济议题上与本土的保守派与改革派持有对应的立场,却全然不知这完全相反。
原因在于,在伊朗的法团主义体制下,保守派集团恰恰是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Bijan Khajehpour 写道:
两伊战争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进入经济领域活动,活动范围超越了军事领域。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Mohsen Rezaei)回忆道,1989 年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将重心转向国家重建。重建期间,主要的政治利益集团都对此表示欢迎。哈塔米时期(1997 至2005 年),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企业开始强行涉足政府项目,伊朗经济中伊斯兰革命卫队经济增长的局限性日渐凸显,尤以 2004 年 Turkcell 移动通信经营执照吊销事件和 2005 年与土耳其TAV公司签订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安全合同撤销事件最为典型。这些项目的合同后来都被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财团。哈塔米时期,伊朗政府不愿让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石油等战略部门。但到了内贾德时期(2005 至 2013 年),所有关键部门都向伊斯兰革命卫队开放,Khatam-ol-Anbia 集团总裁罗斯塔姆·加塞米(Rostam Qassemi)还当上了石油部长...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网络甚至还将触手伸向了足球俱乐部和酒店。如果仔细研究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企业和所谓的由卫队司令官管理的 Bonyad Taavon Sepah 基金会便能发现,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实体已进入伊朗经济每一个可能的分支领域。
类似地,Iran International 在对于 Bagheri 将军的评论当中也指出:
伊朗的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从之前的私有化浪潮中受益颇丰,全部或部分接管了政府出售的许多公司和企业....去年,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显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控制了伊朗多达一半的石油出口,为军事行动和盟友提供资金...该国的新预算允许石油部与第三方签订石油和天然气田作业合同以清偿债务,这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合同将落入所谓的 Khosoulati 实体手中的担忧——这些实体是与统治体系内部人士有关的准国家组织,而不是真正的私营部门企业。
无论如何,伊朗实现了私有化——在这里没有必要纠缠什么是‘真正的私营部门’——这不过是一个如同‘谁是真正的苏格兰人’一样愚蠢的问题。当前的伊朗经济是私人资本与市场主导的,在其中国家的作用日益减少。
甚至‘最高领袖’本人在此也难逃干系:在教士集团手下存在着各式大大小小的‘Bonyads’,即波斯语的‘基金会’,它们在数百年来以‘教产’的形式囤积了大量的财富和土地,且只对最高领袖负责。据 Molavi(2006)的估计,它们总共控制了伊朗超过 20% 的GDP,为数以百万计的伊朗人提供了工作,并且既不缴纳税收,也不受国家监督。
甚至巴斯基也有自己的商业帝国,既巴斯基合作基金会(BCF),Mazaheri(2020)写道,截至2007年,它已经拥有了超过1400家公司,包括伊朗最大的私人银行,Mehr Bank。
但是,让我们切勿以为这仅仅是在豢养一个无比庞大的寄生集团。伊朗的裙带资本主义与法团主义是共生的:它通过法团主义,通过国家经由社会团体中介的社会控制而加强了统治阶级的特权,但是另一方面,又依赖于这些团体的社会性。譬如说,统治集团可以通过宗教下属的基金会而疯狂敛财,但是基金会的运作同时也依赖于信众,为此,这些基金会必须以‘宗教慈善’之名而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相比于巴列维时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巴列维时期的基金会的主要投资对象是富人,而其资产来源则是穷人。伊斯兰革命之后,基金会通过国有化与财产没收而扩充了自身,并承担起了为‘烈士’家属提供保障的职能。批评者常说,在伊朗超过1200万的贫困人口当中,仍有数百万人没有得到来自基金会的帮助,但是,这也反过来说明,有近千万的极端贫困的伊朗人正是依靠基金会为生。
巴斯基的情况是类似的。通过控制企业而获取的经营特权使其积累颇丰,而这当中的一部分则被用于社会投资,为巴斯基成员提供各种社会福利。这自然又会反过来加强他们与政权之间的联系。数据表明,伊朗政府当中超过65%的雇员都是巴斯基的成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朗走上裙带资本主义的道路也是合力的结果:骤然的经济私有化对于底层人民的伤害使他们宁愿让企业保留一种法团主义的控制。Golkar 指出,在 2005-2009 年当中,只有 20% 的国有企业真正落入了私人资本手中,其余则全部被巴斯基等组织收购,但是,这却未尝不受伊朗民众的欢迎。
3
Part.3
结论
本文仅仅试图通过极其有限的资料而还原出一个法团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并共生共荣的伊朗社会的面貌。我们试图理解伊斯兰共和国自身得以长期稳固的根源,并破除对于其诸多妖魔化的想象。对于伊朗社会而言,革命的道路不在于外部,而在于能否利用其法团主义本身所部分保留的社会的自主性,逐步消除国家和统治集团的‘利益绑架’。在另一方面,伊朗社会并非在组织上处于前现代或前资本主义状态,而是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处于畸形的裙带资本主义当中——这种裙带资本主义的出现并非是因为它‘不够资本主义’,而恰恰是源于其‘资本主义化’,即经济自由化与私有化的改革的产物,并由此受到统治集团核心,即俗称的‘保守派’的欢迎。在法团主义的大背景下,伊朗民众通过社会组织而事实上制约了国有资产完全落入私人手中,而是停留在模糊不清的‘集体’控制的层次上。
本文绝非为伊朗政府辩护——神权统治必须被推翻。但是,如果人们只是遵循着一种刻板印象,将教士集团简单地看成是伊斯兰人民革命的‘篡夺者’,忽视其物质的,而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统治基础,它与伊朗人民事实上的联系,我们就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撼动它,无论暗杀多少它的‘高级成员’。伊朗独特的法团主义体制已经将伊朗社会本身凝结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不能简单地通过外国入侵而被废除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另一方面,如果说伊朗人民正面临着苦难与绝境,那么这种绝境正是伊斯兰共和国自身的裙带资本主义体制所造成的,但是,考虑到世界第三世界的普遍处境,绝不应当幻想说在通过‘外力’而毁灭了教士集团之后,伊朗就会摆脱这种状况。在这种意义上,左翼没有必要因为羞于与‘反动的统治者’为伍而放弃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这种谴责与对伊朗的神权统治者的谴责并不矛盾,并且是唯一对于其人民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