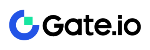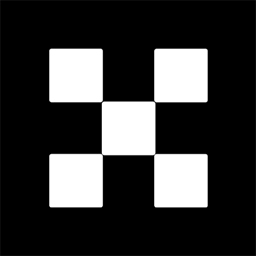自从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所谓“对等关税”的美国经济“解放日”以来,我国政府,学界和民间形成了广泛共识:最好的应对方案是“扩大内需”。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双循环”是在2020年5月23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他说:“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政府就提出了“扩大内需”。当时我在1999年第5-6期“国际经济评论”杂志曾发表“扩大内需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文:


说来惭愧:此文今日读来,似乎还不完全过时,因为论证的要点是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扩大内需。目前,我们“扩大内需”的主要政策是“以旧换新”和“消费券”。但这两者都不如增加居民收入来得切实。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17大报告即已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等的最近研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中国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盛松成文链接:通过再分配提振消费与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增速,也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见“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的文章,人民出版社,2022)。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对特朗普关税战,“扩大内需”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切实采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这件大事可以从“华为模式普遍化”入手。1990年,华为首次提出员工持股的概念,当时职工参股的价格为每股10元,华为税后利润的15%作为股权分红。2001年,华为推出“虚拟受限股”改革,此类“虚拟股票”享有一定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权,但不能转让和出售,离职时即失效。这和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的“职工内部资本账户”概念有一些共同点。

2008年,华为进一步给所有工龄一年以上的职工配股,每股4.04元,如果员工没有足够现金来购买股票,华为以公司名义向银行提供担保,使得职工贷款购买股票。2013年,华为又实施了“时间单位计划”(TUP ,Time-Based Unit Plan),这是一项以5年为一个周期的对中外职工都适用的利润分享计划。华为这一制度安排,属于“初次分配”,但显然不能用笼统的“靠市场”来解释。正如“哈佛商学评论”的一篇文章认为,华为选择员工持股和利润分享,是任正非的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理念所致(“HUAWEI:A Case Study of When Profit Share Works”,https://hbr.org/2015/09/huawei-a-case-study-of-when-profit-sharing-works)。
实际上,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 (任正非本人至今只占华为总股份的1.4%)是在“初次分配”上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详细情况可参见“玖零管理研究院”微信公号以及“华为年报 2019”)在“初次分配”上兼顾效率与公平,使得劳动者能够分享企业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润增长,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当然,我所说的“华为模式普遍化”,并不是说所有企业都必须采用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而是要借鉴华为模式的精神,也即是“十二五规划”(2010年)中已经提出的“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其实,“福特生产方式”的发明者亨利·福特在1914年已经把福特公司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这是当时行业平均工资的两倍,他说这样才能使得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买得起他们生产的Model T 汽车。在“后福特主义”的经典著作“第二次工业分水岭”中,Michael Piore和Charles Sabel进一步论述了通用汽车公司(GM)和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工资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挂钩的合约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在“非凯恩斯国家”的美国实行了“凯恩斯式收入政策”:


在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例之外,应对特朗普关税战,切实“扩大内需”所需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通过“再分配”去吃“福利国家的免费午餐”。“福利国家”是“免费午餐”的重要理论是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学家Peter Lindert 在“增长的公共性”一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提出的:


Peter Lindert的多国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在1880-2000间的社会转移支付(退休金,失业救济金,医保和住房保障等补贴措施)和该国的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大的负相关性,越是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就越发达。这说明“福利国家”是潜在的“免费午餐”,即高达GDP的25%至35%的社会转移支付并没有降低经济增长率,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与这一趋势相反,前面引用过的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等的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低于居民部门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这反映出我国再分配的调节不够合理,且居民部门转移支付支出大于收入,致使再分配后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时”:

也许正是因为我国建立“福利国家”的进程与成为经济大国的进程不够同步,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和中国证监会原主席郭树清都强调提出农民养老金过低问题(平均每月260元)。郭树清说:“可否考虑,统筹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在做实专业化法治化承接机制前提下,划拨更高比例国有资本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主要用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党中央、国务院上世纪90年代就作出决策,动用外汇储备收益和划拨国有资产补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超过2800亿元,作为战略储备资产,并于2000年成立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到目前为止国家社保基金战略储备已达到约3万亿元。2017年,国务院发文明确划拨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10%的国有股权充实社保基金,到去年底已合计划拨3.3万亿元。在做好建账建制工作的同时,建议未来进一步提高划拨比例、增加划拨规模,分期分批、依法依规实施操作,并设立专门的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公司负责专业化运营管理。这么做可以获取多方面的重大效益:宣示强大的改革行动决心;缓解人民群众对老年生活的担忧;实现安全稳健较好收益;有效解决国企产权模糊和股权虚置问题;为专业高效运营国有资本提供引领和示范,等等。”(参见:郭树清博鳌论坛发言全文:养老保险改革的几点意见)。
Peter Lindert认为,“福利国家是免费午餐”的谜底在于,累退的消费税(增值税是消费税的一种)和普遍主义(较少对福利接受者的资格审查)的社会公共支出的政治结合:前者提高了政府的征税效率,而后者则以社会支出的普遍增加去抵消前者的累退性(Peter Lindert,“Growing Publ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p.36)。我国正在完成“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202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增值税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可以理解为给我国1994年开始的累退性的增值税注入普遍性的社会公共支出的“福利国家免费午餐”的另一半。
在初次分配中增加劳动者收入,在再分配中改善劳动者收入,是我们扩大内需应对特朗普关税战需要做的两件大事。但最近迹象表明,特朗普关税战遇到了挫折,因为很多重要产品的供应链都在美国之外(例如,苹果手机的配件很多在中国生产),特朗普关税的自伤程度相当大。他正在对包括中国出口在内的一些产品进行关税豁免。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关税战之后是金融战,特朗普很可能对流入美国的资本征税。最早报道这一可能性的是英国“金融时报”2025年3月14日的Gillian Tett的文章:

关于特朗普关税战和金融战的关系,他新任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Stephen Miran在所谓“海湖庄园协议”里已经做了系统的论述。“海湖庄园协议”的关键是关税,美元和对同盟国的“安全保护伞”的“三位一体”,其主旨是改造布雷顿森林体系,克服“特里芬悖论” (参见第564期|崔之元:Stephen Miran与“海湖庄园协议”)。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在2013年接受Miran的哈佛导师Martin Feldstein的访问时认为,1971年尼克松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特里芬悖论”仍然存在,只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在美国巨大贸易逆差下的不可持续性转化为美国国库券的价值稳定和各国对美顺差(中国首当其冲)所积累的巨额美元之间的不可持续性。



特朗普关税战的部分受挫,不足以改变他改造布雷顿森林体系,克服“特里芬悖论”的决心,因此他很可能下一步重点转向金融战。在“海湖庄园协议”的设计中,关税本来就主要是谈判手段,“对等关税”的数值并非关键。但4月2日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后,出现了一个他没有意料到情况,即国债市场的波动导致市场对美元的储值功能的信心下降。正如2025年4月19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

在货币的三种功能——“计量单位”(unit of account),“支付手段”(means of payment)和“价值储藏”(storage of value)——中,美元的前两种功能比较容易被替代。例如,在巴西与中国的大豆交易中,完全没有必要以美元来记账和支付。但是,由于美国具有流动性和深度最强的国债市场,其“价值储藏”功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仍难被替代:在次贷危机纵深发展之时,美元竟然发生了大幅度升值(数据见Robert McCauley and Patrick McGuire, “Dollar Appreciation in 2008:Safe Haven, Carry Trades and Dollar Shortage and Overhedging”,BIS Quarterly Review, “国际清算银行季刊”, December, 2009)。这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发生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危机总是伴随着货币贬值。“美国例外”的发生,和各国投资者在高度不确定的危机时期寻求“价值储藏”的避风港有关,而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提供了这种避风港——尽管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不高。正如康奈尔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Esward Prasad在其“美元陷阱”一书中所形象比喻的那样:当前以美元为“价值储藏”的国际货币体系像一座沙丘,各国已经认识到其基础不稳,但仍然不得不继续维护这个体系,以免沙丘的倒塌伤及自身。但这次特朗普关税后美元的下跌,显示出国际市场对美元“价值储藏”功能的怀疑的加深。
著名国际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等人用“原罪”一词来比喻发展中国家本币的长期国债市场不发达以及无法用本币在国外市场发债的情形(Barry Eichengreen, Richardo Hausmann and Ugo Panizza, “The Mysteryof Original Sin”, working paper, August 2003)。当然,发展中国家克服“原罪”并不容易,甚至连欧盟至今也还没有能够发展出统一的“欧洲债券”(Eurobond)。可喜的是,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五国的“新发展银行”已经把克服“原罪”当成了重中之重。2017年,我应“新发展银行”之邀为金砖五国厦门首脑峰会提供背景报告,其中建议“新发展银行”借鉴“亚洲债券基金2”(ABF2),以之作为美元“价值储藏”功能的替代。

“亚洲债券基金2”是在新加坡注册的“单位信托”(unit trust),并在香港股市上市。它由9个分基金构成,8个基金是单个成员国基金(包括“中国基金”,“中国香港特区基金”,“印尼基金”,“韩国基金”,“马来西亚基金”,“菲律宾基金”, “新加坡基金”和“泰国基金”),而第9个基金则是上述8个基金的指数基金,其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对具体债券产品了解不多的被动投资者(技术术语是“iBoxx Pan Asia Index, 详见Chan, Eric et al.“Local Currency Bond Markets and the Asian Bond Fund 2 Initiative”, BIS PaperNo.63, 2010)。我们可以设想,金砖五国也像“亚洲债券基金2”一样,分别在各成员国建立债券基金,同时再建立五国的“债券指数基金”,这将使金砖五国在克服“原罪”上迈出更大一步,逐步替代美国国债市场的“价值储藏”功能,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多极化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现在看来,我在2017年提出的这个建议,也正是我们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战和金融战所需要做的第三件大事。在2023年金砖国家扩大成员后(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五国正式加入),用“亚洲债券基金2”来逐步替代美元的“价值储藏”功能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特朗普开展关税战和金融战,是为了兑现他“使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竞选承诺。
如果我们应对他的挑战时做了本文所说的三件大事,就可以坏事变好事,“使中国再次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