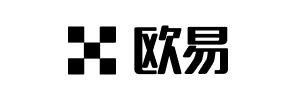口述者:文化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卫生院医生张瑞丽
采访时间:2018年1月8日
问:张阿姨您好!请问您是哪一年到向阳湖的?
张:我是1970年6月到向阳湖的。
问:以什么样的身份到向阳湖的呢?
张:1970年,我从北京军区251医院转业,正好29岁,随20来个军医一起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后来军宣队给我们看了领导批示,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让一批军医到向阳湖,为的是给一批老干部、学术权威、艺术家看病,保证他们的健康。
我爱人也是一个军医,我们一起带着孩子来到咸宁。我爱人叫贺天喜,是个中医。我们家第二个孩子就是在咸宁出生的。
问:卫生院的总部在甘棠么?卫生院还有些什么人?
张:是的。我们卫生院的两个老主任当时快六十的,一个姓赵,一个叫余启文。他们是原国民党的军医,在解放军这里属留用人员,也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咸宁。
问:您在向阳湖多长时间?
张:我在向阳湖两年,我爱人到1973年10月才回北京。我提前回北京是因为孩子读书等问题。
问:能说说您眼里的干校生活么?
张:我们在干校卫生院特别忙,因为干校老同志多,劳动强度大,病号也多。比如郭小川,当时神经衰弱,经常找我们。还有周蘶峙,高血压,还有李季、孟超、侯金镜等人。
干校的劳动很累很苦,新开垦的田,淤泥很深,很多女同志插秧的时候,如同坐在水田里,妇科病比较多,很心疼她们。大家劳动起来,穿着短袖子,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达到60度,很多人的膀子晒伤了,脱了皮,有些人中了暑。这些人原来没有干过农活,或者很多年没有干农活了,但是劳动起来,真是能干,真是不怕苦,让我们很感动。
当时干校缺少医药,我爱人的针炙发挥了很大作用。我记得司徒慧敏,身上疼,经常找他扎针炙。司徒当时就穿个破棉袄,棉花都露出来了,腰上捆个草绳,一点也不像个大干部,特别亲和的一个人,有时跟我们讲三十年代上海电影界的故事。
干校文化人多,时间一长,大家就写诗夸我丈夫:贺大夫扎针,针针入穴,把人扎得死去活来(就是“死”去了,“活”来了)。
当时农民很穷,也找我们看病,比如阑尾炎手术什么的,我们也帮他们做。他们没有钱来挂号,就带些鳜鱼、王八什么的,我们也尽量不收钱或者少收钱。有一个农民,瘫痪了,找我爱人扎针炙,后来可以走了,可以劳动了,很开心。
干校经常放电影,比如《卖花姑娘》什么的,在干校的广场放,农民们也来看,早早地就过来等。
刚到干校的时候,生活比较苦,吃那种糙米,红色的,味道不好。菜也不多。后来自己种地、养猪什么的,一步步好了起来,到后来生活就比较好了。
我们也经常下连队,各连队都有卫生室,我们培训他们的卫生员,后来很多卫生员,成了专职的医生。比如故宫有个小何,跟我爱人学针炙,后来回到故宫后,就在卫生室工作。有时候,我们与咸宁的军区医院,195医院,也有些业务往来。
当时干校还有两个剧团:红旗越剧团、勇进平剧团,经常排些节目,有宣传队的性质。
最早离开干校的应该是一些文物专家,为的是尼克松要访华,需要做些准备工作,文化上的准备。
我记得当时文化部改叫文化组了,人比较少。
问:您觉得向阳湖带给您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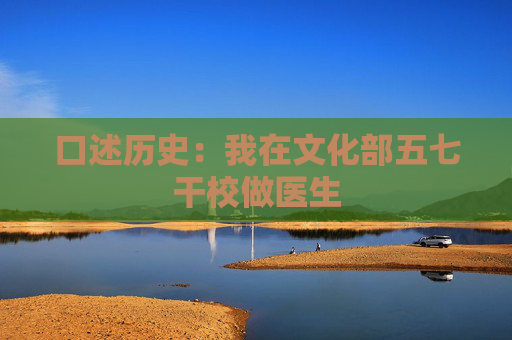
张:现在回忆起来,很美好的。认识了很多文化人,当时他们是被专政对象,但是我觉得他们人很好,很有素养。我觉得在我的青春年华,有向阳湖的经历,很珍贵,很值得纪念。咸宁山青水秀,空气好,是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们特别怀念那里,怀念那处土地。
感谢你记录我们的历史,我在想,如果时光可以穿越,我愿意再来一次向阳湖。
采访后记:一接通张阿姨的电话,她明亮的嗓子就告知我,老人家身体还不错,而且性格热情开朗。言谈中,对向阳湖是满满的情感与思念。我们一边电话交流,贺老一边在边上补充,两个人的对话,变成了三个人的交流。(本次采访由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罗勇,以及黄玲丽和宋冀辉老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