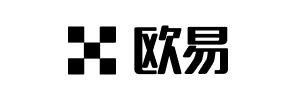在那个动荡充满未知的年代,在陕北黄土地的窑洞前,一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用旁观者那冷静、客观但又带着些幽默的笔触记录了一群被称作“赤匪”的中国革命者的真实面容时,他或许没有想到,这本《红星照耀中国》会在近九十年后依旧照亮着今天的我的精神世界。
作为被人们称为“Z世代”的一员,我在国企改制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中出生、度过着自己的整个未成年时期,“下二代”成了任何人都无法撕下的一张自我标签,所以物质丰裕的生活从来与我无关,但同一代人都有过的精神迷茫我却不曾缺席。因此,当一头齐颈短发的我在第一次在初中老校园的那间小小阅览室翻到这部角落里因蟑螂啃咬而封面破损的作品时,我便被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革命故事所深深吸引,并为它而办下了我这一生中第一张借书卡,那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它会在我的生命经验中熔铸出新的精神图谱。它带领我一路走进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不仅让那些史册上的名字鲜活了起来,而且让我看到了在那个黑暗的夜空下依然没有放弃闪耀的颗颗繁星,更在今天我们这一代青年普遍存在的困境中,开辟出一条树立精神信仰的可能路径。

那是一段星光璀璨的岁月,那是一群在那块土地上不懈斗争着的人们,他们都有着朴素却纯真的笑容和干净却明亮的眼睛,以及,同一个简单而坚定的信仰、平凡而伟大的目标。
埃德加·斯诺把那段岁月、那片土地、那些人的点点星光写进了书里,也开创性地将那些从未被公开报道过的组织形式、生存现状和长远的政治追求都一一做了自己的阐释。
即使在近九十年后的今天,当坐在收银台前利用间隙的我阅读着书里的文字时,我甚至因为带有触动力的细节而感觉到时间的凝滞,让我仿佛与书里的那些人儿产生了感应。
在延安抗大的课堂上,斯诺看见了这样的场景: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在沙地上画着几何图形,用“树枝牌”圆规研究战术理论。这种“用最原始的工具追求最先进知识”的图景,让今天的我们在手机、电脑包围中的知识焦虑产生了一种自愧不如之感。当现在的我拿起一个小巧精致的铁制圆规却画不好一个最简单的圆时,当理论知识获取变得好似轻而易得却因浮躁失去思考深度时,心浮气躁的我突然发现革命年代那种“带着泥土味的求知欲”反而展现着它惊人的现代性价值。
那群红军战士,大多有着红扑扑的脸蛋、亮闪闪的眼睛、好像用不完的精力、真诚爽快的性格,就连“红小鬼”们如何将一些人看来略显生硬的政治理论转化成通俗易懂的顺口溜都带有一种珍贵的泥土气息的可爱。
即便那段岁月里的每个人都不想轻易谈起自己的个人功绩,但一个优秀的、有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斯诺使用了他“精于套话”的功能,他想从他们的口中获得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亲友的故事、他们同志的故事。
他成功了,凡是与他深谈过的人,都和他讲出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家庭出身、他们参加革命前的经历、他们参加革命后的经过,即使故事里带着饥寒交迫、血泪交加,他们都是那样平静地、就像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轻描淡写讲了出来。他们中有如今已被反复研究的毛泽东、彭德怀,也有当年那个被蒋介石给出一等赏金、缺着两个门牙还带着一脸孩子气般笑容的徐海东,甚至是那一个个未能留下名字的“红小鬼”。
斯诺把他的努力成果写到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日记本里,换来了他心中对那段岁月里的红色政权最真实确切的感受,换来了让因国民政府横加阻绝、舆论控制的人们想要倾听的真实的声音,更换来了今天的我回看那段历史时的一个有力佐证。
斯诺留下了那段岁月里用最真挚的感情对待身边每一个人的毛泽东之前并未为人知的过去,而在几十年后整个中国几乎都洋溢着红色激情的年代,斯诺最后一次来到了中国,同样用他真实、客观的手中笔写下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他时的谈话,以及他在各地访问时看到的因那场大革命而引起的深刻变化和他对一些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把它们放进了自己最后一部也是一部未尽的作品——《漫长的革命》中。即便,它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主流宣传所刻意忽略以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它还是成为了全世界甚至我们自己擦亮眼睛、细窥那个时代的中国的一个窗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是《红星照耀中国》的续集。
当我第一次读完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在初一夏天的历史课上,书就被我放在历史课本底下偷偷地读,读完后坐在靠窗第一排的我因为怕被老师发现就把书本抽出来放在腿上,过了一分钟老师布置了课后作业下课铃就响起了,听着铃声看着不知怎么合上的书本,捧起还带着一点温热的它看着残破封面上黑体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我都不敢相信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感觉就像穿越了时空一样。在那个时空中,我的思绪随着书里的人们一起放声大笑、一起悲伤落泪、一起焦虑紧张,而从那个时空中再回到现实,则是那样让我无措甚至惊惶。
当我看着借书卡上阅览室老师把“已归还”的红章盖到写着书名那一行字上时,我突然意识到书中那些充满稚气、活泼率真的“红小鬼”们,其实年龄上和我一般大小,他们或许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身死牺牲,不知埋骨何处,甚至是尸骨无存。
当我读到更多的书时,我了解到那个在斯诺笔下“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的毛泽东在几十年后的那场漫长的革命中却会为一句“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而失声痛哭,当时我想到几近落泪也想不明白的是当年那段岁月里仿佛闭着眼睛都可以看到的目标、那些仿佛在空气中都可以触摸到的希望、那些即便爬雪山过草地和吃草根啃树皮也没有动摇过的理想、那些甘愿为之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信仰,到底是在哪一时哪一刻哪一分哪一秒就通通都变成镜中花、水中月一样成了某些人口中“虚无缥缈的东西”而从我们眼前既看不见、也抓不到了呢?
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一句“人性如此”就让它们在官僚权贵的别墅豪车、西装红酒、血统高贵代代传中被碾得粉碎么?不,不是,不是这样的,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其中也包括所谓的“人性”,高高在上的他们才是要在历史的螺旋上升中落得天街踏尽、声名狼藉、化为齑粉的下场。
因此,尽管时代背景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但《红星照耀中国》所体现的革命精神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年的革命者们面对黑夜把自己划作一颗颗繁星来照耀中华大地,今天的我们同样应该沿着他们的血脚印前进以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革命事业中,方不负曾经照耀在历史天空下的熠熠星光。
2025年5月10日于云南曲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