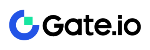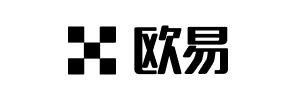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三)“左圈”分子所重复犯的历史错误
“左圈”的这种“标新立异”事实上也只是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斗争运动的重演罢了。他们所提出的观点、路线与策略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并着手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进行反抗德意志帝国的革命时就已经有人提出过,我们可以通过当年由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合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看到“左圈”分子们在重复当年的小资产阶级哪些错误。
马恩二人在该信中开篇就提到:“弟兄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1848年三月运动之后,资产者果然是立刻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去迫使工人即自己的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他们从前的被压迫的地位。”当时德国的封建势力可以说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工人阶级的共同的敌人,为了推翻这个反动势力的统治,当时尚未觉悟又尚未被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先锋队所领导的德国工人阶级们自发地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结果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使德国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牺牲品,因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一旦革命运动现在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时,就可能由于政府发生财政困难而使统治权终于转到它手里去,而使它自己的利益有所保障。”这就已经充分说明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走的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对立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只能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工人绝对的压迫和统治。(在封建势力顽固的国家尤其是被压迫国家中,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依靠与封建势力妥协并进行联合统治而实现的,例如二月革命之前的俄国。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所取得的统治(现在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扮演着当时取得统治权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角色)迫使德国的工人阶级必须再次发动革命已真正实现德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遭到德国资产阶级专政压迫或对革命结果失望的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中的进步者们(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则扮演着这个角色),便“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完全就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在马恩二人看来,这些“社会主义者”正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扮演着“德国自由资产者于1848年在和人民的关系上所扮演过的叛徒角色”,“而民主的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方面所处的地位,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地位相同”,而他们所组成的党派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更为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他们的政党从原有的名称改为“红色共和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证明这个党现在已不得不反对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依靠无产阶级。”正如取得统治地位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一样,这些大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所需要的是保存自己阶级的政治地位,保护自己在资产阶级专政中的利益而已,他们对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是不可能诚实的,“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
对于小资产者向工人阶级靠拢的行为,马恩二人无情地揭穿道:“目前,在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和协调,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党内一切派别的巨大的反对派政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了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特殊要求。这种联合无疑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而只对小资产者有利。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极坚决的拒绝态度。”无产阶级真正要做的不是附和这些人,“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
而到了列宁时期的俄国无产阶级斗争,小资产阶级派别对无产阶级运动也不见得有什么进步,他们所犯的错误也是现今所谓“左圈”分子所重复犯的历史错误。小资产阶级或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工人贵族阶层机会主义势力主导了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为代表,“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这一点现在“左圈”在口头上是承认的,而在他们的观点、策略和实际行动中却是忽视甚至是否定的。——笔者注);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左圈”在他们所规划的路线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左圈”用群众和XX的对立这一空洞的概念掩盖了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列宁《怎么办?》)
“左圈”分子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一样,存在着同一种固有矛盾,也就是“左圈”第四个固有矛盾,即无产阶级先锋队所需要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与小资产阶级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就容易倒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一边,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忽视、轻蔑、扭曲、割裂甚至是完全背叛。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漠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否定,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偷换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轻蔑与背叛在他们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左圈”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轻蔑与背叛则更加明目张胆,还有因处于对历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而鼓吹托洛茨基、毛泽东、邓小平一脉相承的XX。在一些“左圈”分子所掌握的各大QQ群、贴吧、论坛中,我们可以到处看到托洛茨基分子、第二国际追随者、工联主义分子、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西马派分子甚至是完全倒向“右派”的日杂、美分等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毒瘤,其中也不乏自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可奇怪的是这些“正统”们居然还可以和这帮毒瘤们和谐相处,互称同志,“左圈”分子们在这方面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
“左圈”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性,决定了“左圈”必然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由此他们一切特有的策略和路线,正如列宁对第二国际的策略和路线以及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扼杀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指导性作用所批判的,“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列宁《怎么办?》)
列宁当时对伯恩施坦等人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批评道:“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制发展程度较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这么热心地、迫不及待地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作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为此,列宁谈及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理论斗争的意义:“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的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决不能那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远没有结束。……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还提及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所写下的教导:“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这样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列宁《怎么办》)
我们可爱的“左圈”分子们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一样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漠视甚至随意玩弄马克思主义,结交任何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却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人,而自己本身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彻底的背叛,因此他们就不明白进行理论宣传掌握无产阶级的重要性,而去推崇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推崇群众的革命冲动,推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无原则的联合。接下来我们看看“左圈”分子所重犯的工联主义者推崇自发性的历史错误。
当时沙皇俄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开始形成,随着俄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越趋尖锐,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为争取阶级利益而进行斗争,他们从最开始的简单粗暴地捣毁机器到1896年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后普遍的罢工,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渐渐趋于成熟,但仍然是自发的斗争,俄国无产阶级仍然是自发的力量,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受科学理论的指导,也没有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前进。工联主义者们醉心于崇拜俄国无产阶级这种自发性,便用“经济主义”即以排斥政治单纯追求经济斗争的方式扼杀了俄国无产阶级真正的政治要求,反对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参与对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领导,而在不得不面对无产阶级政治斗争路线的问题,在当时即无产阶级如何完成消灭沙皇专制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又用把无产阶级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尾巴主义来搪塞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变成俄国资产阶级实现自己政治阴谋的棋子。
列宁对此批评道:“‘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而来的。……(个人不对阶级关系负责,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社会主义社会的萌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一样,是从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说的理论的批判形成的,这就需要有主动站在无产阶级这边,并时刻忠诚于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解放的有产阶级知识分子。——笔者注)
“……反对任何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取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
“……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这一精彩的批判是多么符合现在“左圈”分子的斗争策略和路线啊!
为了纠正对自发性崇拜的错误,列宁提出:“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任何放弃或轻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推崇无产阶级自发性,而去谋求和资产阶级派别合作的想法都是危险的,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越是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就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所蛊惑。(列宁《怎么办?》)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人根据科学而深邃的洞察和他们的睿智,阐明了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以及如何组织起无产阶级使其成为独立自觉的革命力量的策略,这是重复犯鼓吹工人阶级自发跟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尾巴主义错误的“左圈”分子所不能理解的。他们更加不能理解的是,马恩列时代的无产阶级所遭遇的情况比现在更糟糕,因为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熟,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远没有今天这样丰富,尤其是马恩二人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经验几乎为零,那个时候马恩列三人依然强调必须组织无产阶级独立的力量以实现无产阶级的独立斗争,而不是附和无产阶级以外的派别,甚至是充当他们的尾巴。而现今我们已经有比当时更成熟的先进且科学的理论,即已经由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根据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也积累了无数次斗争和专政的经验,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已经步入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并且越来越处理不了自身所造成的危机,再加上如今信息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使计划经济实行的可能性与科学性上升到可预见的地步,无产阶级更应该可以而且很快从被冲散的状态重新组织成为自觉的革命力量,“左圈”分子所规划的尾巴主义路线,只能是历史可笑的重演而已。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左派”(因为坚定的、彻底的左派最终必然趋于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就个别和策略性的问题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但绝不该借此鼓吹什么“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类的调子。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有限的支持和合作(例如与某些真诚地关心劳工问题的“维权团体”的联系,有助于增大我们争取工人的几率。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工人斗争问题上,我们的方法和路线与自由派的意愿却依然是真正的竞争关系。),绝不是为了掩盖或推延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必然矛盾和分歧,只是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决战扫清道路,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的极度有限的合作,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坚持原则和立场,并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的坚决斗争这一前提条件下实现的,而不是靠空谈的求同存异、附和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相互学习,这种历史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势力的“左圈”分子所不能理解的。

那么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左圈”分子他们为什么会重复犯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智慧不足”吗?如果我们回答是,那么我们就和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也鼓吹智商差别论,从空洞且简单粗暴的“强智”和“弱智”出发解释立场、认识和路线的分歧。问题不在于智商对立场、认识和路线的决定作用,相反,正是立场的不同决定了认识、路线以及对世界对社会的根本看法的差别。“左圈”分子背叛了无产阶级,选择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其认识、路线自然是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左圈”分子重复犯了以往小资产阶级的错误,除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至今,它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内容并没有改变,即社会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农民等中间阶层游动于两者之间并且在阶级消灭前就已经趋于消灭这一根本内容至今并没有改变而已,除此之外,就什么都说明不了了。
要彻底说明“左圈”分子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为什么重复犯已经失败无数次的小资产阶级错误,就应该从“左圈”分子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寻找答案。由此,我们转入了对“左圈”分子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探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