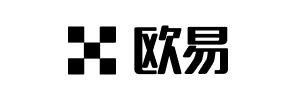坦白地说,专业历史学家当然不可能发觉不了“帝国”有适用性方面的不足,但是面对业已存在的混淆和误读,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不应局限为内行人士的阳春白雪,具备专业素养的学者有义务为大众努力厘清盘根错节的概念。
在史学研究中,一些充满问题意识的论题,经过学者详尽举证后,往往呈现一种“错位”感。即便不将史学研究的目标在一开始就设定为“求真”或“经世”,论者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应以何种视角面对复杂的历史叙事?关于“帝国”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就是典型。
概念“适用性”带来的“错位”感
漫长的历史造就了汉语词汇极大的丰富性,所以当今许多流行的源生于其他文明区域的概念,如果“求同存异”,则不难在中国历史中找到相应的锚点。但谈及“帝国”时,无论古今东西,只能共用一个单向流动的时间维度。人们选择历时性地上溯,实际上是为了当下和以后的空间利益。基于此,在历史学领域内,只有理解历史情境中“空间”的作用,才能体察出更完整的历史叙事细节。例如,无论多么强势的政权,都只能建立在空间维度之上。古代中国的基本理念——“大一统”,就曾被狭窄地理解为“大统一”。而与“大统一”对应的历史范畴,又基本归于“疆域”。在一些宽泛的历史理解中,具备广袤“疆域”的政权,自然意味着强大实力。当学界将东西方历史上的政权对标时,把“帝国”冠之以古代中国,似乎理所当然。
然而,“帝国”的含义和适用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对于历史“空间”的理解,也不应局限于政权的版图。广义地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后,人们愈少用“帝国”来界定各国的政权属性。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挂钩讨论,西方自由主义者将个体权利视为文明进程的唯一标尺之后,更广泛的应用情景是:行“帝国主义”之实的政权,纵然其政体不符,亦为“帝国”;相反,如果仍实行传统意义的帝制,但无法占据国际话语权、昭示出“帝国主义风采”,则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帝国”。也就是说,“帝国”一词的适用场域,几乎不再是政体评判,更多成为一种暗含贬义的标签。
此“帝国”非彼“帝国”
可能有人会说,古代中国的皇帝自认统驭“天下”,既然“天下”都是其囊中之物,难道不是最标准的“帝国主义之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空间本身是绝对存在的,然而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却在变化。
在古代中国的视角下,“天下”是一个非均质的整体空间,包括核心区域“中原”、“九州”和位于边陲的“四夷”、“海外”。在很多情况下,古代中国的皇帝只要“四夷”保持名义上的“臣服”。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皇(王)朝在处理“藩属”关系时,不倾向掠夺“臣服”区域的资源,反而是厚往薄来的情形屡见不鲜。尤其是随着北方民族政权不断崛起,甚至入主中原,中原的皇(王)朝对所谓“蛮夷”的评价也大有改观,以至于元明鼎革后,明太祖朱元璋公开声称继奉元朝正统,称元帝为养天下者。
必须指出,在近现代以来辉格史观的语境中,秦汉和罗马常被一些人视为“帝国”样板,这与嬴政、刘邦还是屋大维怎么看待自己的尊号已关联不大。在西方历史认知中,罗马帝国被认为具备一定“普世帝国”的特点。不过,罗马帝国的权力结构和模式与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政权明显不同,最迟自其东西分治开始,欧洲的核心区域长期未出现能够稳定控制各地的政权。虽然其海外殖民活动声势浩大,但多数“强势”政权长时间实现不了欧洲“疆域”的统一。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也在某些时期如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辽宋夏金并立时期没有实现统一,然而对统一的追求通贯自秦至清的历朝历代。

唐蕃会盟碑是唐朝和吐蕃为纪念长庆元年(821年)会盟成功而立的纪念碑,碑文包含汉藏两种文字,是中国“大一统”王朝处理边疆关系的生动写照。图为唐蕃会盟碑拓片(局部) 视觉中国/供图
简言之,古代中国和西方即使同样幅员辽阔,但其各自幅员的重心差异相当明显。如果广阔幅员被当作近现代“帝国”叙事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这种差异就不能被忽视。这也是为什么在相关话题下,我们必须重点关注地理空间对于政权合法性的意义。古代西方基于自治权利而“强大”的联合体,并未孕育出与古代中国相近的权力结构和空间认知。那么,若将古代中国视作“帝国”,长期无法一统欧陆的列强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反而没有资格被称为“帝国”。何况古代中国真正的价值理念“大一统”,除却控制范围(“大统一”)之外,还要求历法、文字、度量衡等各个方面的“一致性”或“统绪性”,与古代西方相比,差异就更大了。
有人认为,“帝国”只是一个泛指,用来指代古代东西方的普遍性政权,其含义大致等同于“国家”,只是这类“国家”实行帝制而已。不过,如此一来,“帝国”也就变成“帝制国家”的简称,无法再用文献中的“帝国”作为“帝制国家”的证据。事实上,看似更“现代”、更普适的“国家”概念,有着和“帝国”相似的问题。“国家”同样曾出现在早期汉语中,当时的“国家”是一个并列名词,并不过分突出二者的从属关系。如今我们所说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是“民族国家”的缩写。“民族国家”是标准的偏正名词,其含义大概贴近“属于某些民族的政权形式”,与中国古籍中的“国家”有本质区别。若不对二者进行区分,而是按照部分人的理解,“行帝国主义之国”通过简化限定条件(设有帝制)而扩大了概念外延,成为可以用于不同时空的“帝国”,那么“民族国家”同样可以借助隐藏“民族”属性,成为可以用于不同时空的“国家”。照此推论,只要有“皇帝”,哪怕并未行“帝国主义”,也被认为可以称作“帝国”。
那些在近现代以来具有先发优势的“帝国主义之国”,却将“帝国”之名强加于曾经有过长期帝制传统、国力又日益增强的其他国家。值得深思的是:缺乏长期帝制历史的“帝国主义之国”反而更易于摆脱历时性上溯的副作用;而被扣上“帝国”帽子的国家则发现,悠久的历史和后发的劣势使他们很难摆脱前者甩过来的帽子。在此背景下,他们是应努力辨清历史叙事的差异,建立独立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以期讲清楚自己的历史?还是应该“海纳百川”,任凭近现代方才建构的历史叙事反攻倒算两千余年的来路?如果没有“帝国主义”,那么讨论古代中国是不是“帝国”或许无伤大雅。同理,如果没有“民族国家”,那么今古政权都可以被泛称为“国家”。只是,史学允许假设,历史却没有如果。
概念统合与甄别
考虑到“王朝”已经成为描述古代东西方政权的术语,或许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概念和词汇,既能普适学术又能让人清晰地感知共性之余的差异。选取“皇朝”一词来替换“帝国”和“国家”,作为更具备精确指向的概念,或许是可行的。虽然古代西方的统治者亦被译作“皇帝”,其政制被称为“帝制”,但与中国终究是异大于同,其对“王”的使用频率更高,且其“皇帝”的权力空间结构等诸多方面也与古代中国明显有异。那么以“王朝”指代古代西方政权,以“皇朝”描述古代中国政权,既不至于掩盖历史的普遍性,又能体现多样性。
在研究东西方历史时,当前学界存在忽略概念古今差异的情况。如在城市史领域,古代中国的城郭或城池虽然看上去与“城市”没有太大差异,但如果做不到在研究古代城市时,时刻意识到不能将极具现代意味的“城市化”作为衡量其演进的唯一标尺,而笼统地称为“城市”,就会埋下一定的学理隐患。比如,既然古代中国有“城市”,那么有没有“市民”?若退一步,姑且说有“市民”,那么有没有“市民权利”?如果继续让步暂时承认有“市民权利”,那么当问题最终叠压到东西方城市既然都有一系列的前置条件,那为什么呈现的具体演进过程以及对政治经济模式的影响却有很大不同?类似的连锁问题在研究进程的后端,往往需要耗费相当大的力气去“打补丁”,归根结底在设立概念时就留下了隐患。事实上,城市史领域的诸多先贤,早已认识到上述问题,如不避麻烦地提出“古典城市化”,以示与现代对应概念有所区别。在其他研究方向,诸如前文提及的“疆域”,相关研究中亦出现“有疆无界”、“差序疆域”、“有限开拓主义”等描述,如果不是“疆域”的适用性所限,在实际研究中也不必增费笔墨。然而,在巨大的学术惯性下,学界尚缺乏对既有概念进行更新的勇气,导致时至今日,很多类似的情形仍在困扰着新一代学者。
再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在非专业人群看来,三角梅繁密的彩色观赏部分即是“花”。可在植物学家看来,只有符合生物学意义的、掩藏在彩色苞片簇拥中的一小部分,才属于真正的花。拉丁学名确实艰涩,但哪怕给三角梅起并不文雅、普适度不高的别名——“叶子花”或“光叶子花”,也至少会对深化非专业人群的三角梅知识有所助益。坦白地说,专业历史学家当然不可能发觉不了“帝国”有适用性方面的不足,但是面对业已存在的混淆和误读,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不应局限为内行人士的阳春白雪,具备专业素养的学者有义务为大众努力厘清盘根错节的概念。
最后,让我们回归史学理论的视角,简要梳理概念使用背后的方法论。历史学研究有两种基本理路,一者为朴素的“顺时而观”,放在本题中即为应考虑古人怎样看待其政权性质,这也是为何绝大多数学者都会从史料中查找“帝国”、“皇(王)朝”、“国家”等概念的出典作为立论之本。与此同时,由于人类认知的滞后性,一种颇具“穿越”色彩、站在前人肩膀上回看往事的“后见之明”同样具备价值。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多元化”、“多样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注意避免陷入归纳法的窠臼。史料卷帙浩繁,必然同时存在大量正例和反例,容易陷入不停举证、机械反驳的死循环。况且,不同于自然科学,历史学无法生存在“真空”之中,解决许多基于错综背景的重要问题,并不能过度依赖复杂的模型和纷繁的限定。由是,泛化概念、融合概念则成为将各种观点得以放置在同一讨论平台的下意识之举。然而,在共同平台建立之后,学人仍会追求概念层面以上的逻辑多元、范式多元、体系多元、认知多元。想要实现这些不同层次的“多元”,终究会回过头来要求更“严苛”的基本概念界定,用以支撑逻辑、范式、体系、认知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的分化与演进。以“皇朝”替换“帝国”、“王朝”,是一个带有理想化色彩同时具备勇气的尝试。相信在未来,在更多的研究方向,定会出现更精当的概念演进,来取代从前的权宜之“词”,那会是绝大多数人都喜闻乐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