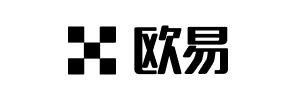刘继明老师在人境院第二期写作研修班开班式上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写作过程中要过好三关,即感情关、语言关、立场关,笔者觉得这“三关”是一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关系,打通了这三关,犹如打通了人体的任督二脉,所流的血、所激发出的灵感、所喷薄待发的文字,都与被压迫的人民、都与无产阶级的命运沉浮息息相关。情感关与语言关,其要旨在于磨砺技巧,精进表达。情感关之跨越,需写作者如海绵吸水,沉入生活汪洋,积累无数真实的哀乐悲欢。语言关之锤炼,则是一场永不停止的词句体操。语言实为技艺,千锤百炼,其光自现。此二关虽需汗水浇灌,却终究能循法精进,终臻化境。然而立场关,它非止步于技巧之域,更直指阶级意识深处——写作三关之中,唯立场关最为本质,最为艰难,亦最为关键。
立场关即阶级关,此关之要义在于为谁立言,为谁发声。写作非无根浮萍,它必然扎根于特定阶级土壤。立场关之艰难,在于它要求写作者勇敢剖析自身阶级印记,自觉向先进阶级靠拢,实现灵魂深处的“脱胎换骨”。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陷于个人情感漩涡,其笔触或哀婉或狷介,然视野多囿于一己悲欢。鲁迅先生早期亦曾经历“彷徨”之痛,但最终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决绝,投向劳苦大众怀抱。只有建立阶级关,才能成为无产阶级写手和战士。
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主席进一步阐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主席的论述深刻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奠定了他领导革命的理论根基,其核心在于揭示阶级斗争是文明史的主轴,而“胜利”与“消灭”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历史前进的逻辑。人类文明史的本质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某些阶级通过斗争取得胜利并建立统治,而另一些阶级则在斗争中消亡。历史进程由阶级力量对比的演变推动(如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
阶级叙事不仅是历史的核心精神,也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离开了阶级叙事,正如列宁所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非阶级的社会主义”通常指那些试图描绘一种超越阶级矛盾、调和所有阶级利益的“和谐”社会主义图景的学说(如某些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列宁认为这种想法是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胡说八道”,它要么是有意欺骗群众(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要么是天真地无视现实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阶级对立和剥削关系。在阶级社会尚未被消灭之前,谈论抽象的、超阶级的“社会主义”或“全民利益”,实际上掩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麻痹了无产阶级的斗志。阶级分析是理解社会、政治和历史的钥匙。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主要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关系),阶级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只要存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阶级分野就不可能消失。任何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实践,如果脱离了阶级视角,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自己的专政,并最终消灭阶级、实现无阶级社会的目标。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毛主席在晚年千叮咛万嘱咐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可惜,毛主席仙逝不久,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阶级斗争,从此劳动人民的地位一落千丈,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否定阶级斗争、阶级叙事的岁月里,无产阶级的手脚被牢牢捆住,资产阶级却拿起了阶级斗争的武器,对无产阶级进行了肆无忌惮拿捏和碾压。只不过他们没有用阶级斗争这个词,但时时处处都在体现“阶级斗争”。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喊,这绝非仅仅是政治策略的召唤,而是为一种被遮蔽的存在赋名。阶级叙事如同烙印在历史肌肤上的深痕,它是无产阶级在漫长岁月中用以辨识自身存在、确认自身力量的底色。阶级叙事之于无产阶级,恰似血液之于生命,是其身份得以确立、历史得以展开的根本坐标。当工业革命的浓烟遮蔽了英格兰的天空,机器轰鸣取代了田园牧歌,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体被抛入历史的舞台中央——他们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一无所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冷峻的笔触描绘了曼彻斯特的景象:工人蜷缩在污秽潮湿的贫民窟,“每一寸空气都混杂着腐烂的恶臭”,超长工时榨干了他们的青春,工伤与疾病如影随形,童工与女工在机器的吞噬下形容枯槁。这绝非孤立个体的不幸,而是整个阶级在血汗与屈辱中的集体诞生仪式。无产阶级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其命运就被刻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被系统性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的劳动不再是自身力量的延伸,而是被异化为替他人增殖财富的冰冷工具,成为资本积累这部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可替换零件。阶级叙事赋予无产阶级的,是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它使工人们看清自己为何在机器的轰鸣中精疲力竭,而财富却源源不断流入另一个大腹便便者的口袋。
阶级叙事更是无产阶级抵抗压迫、锻造团结的精神熔炉,赋予其变革世界的集体意志与行动力量。在《国际歌》那悲怆而雄壮的旋律中,“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呐喊,正是阶级意识觉醒的震撼回响。它超越了地域与行业的区隔,将千万颗破碎的心熔铸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洪流。巴黎公社社员在街垒上浴血奋战的身影,十月革命中“和平、土地、面包”的朴素口号,无不凝聚着阶级叙事的巨大能量。它使工人从“自在阶级”迈向“自为阶级”,从被动承受命运的个体,转变为主动创造历史的主体。这种叙事如烈火般点燃希望,赋予他们挑战旧秩序、创造新世界的勇气与决心。在当代语境下,阶级叙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消解与重构。一面是“阶层”话语的悄然替换,将结构性的压迫关系模糊化为个体流动性的统计图表;一面是消费主义编织的华丽幻梦,鼓吹“中产神话”引诱人们沉醉于符号消费的迷狂。当“打工人”的自嘲为牛马,在网络空间弥漫,其背后固然有对现实处境的无奈认知,却也暗含对阶级身份模糊化的顺从与接受。资本与技术合谋编织的新神话,试图以“知识工作者”、“创意阶层”等光鲜称谓,覆盖无产阶级生存的本质——依然被资本逻辑所支配,其劳动成果依然被无偿占有。
在阶级叙事被宣布“过时”的喧嚣中,其潜藏的生命力的不断顽强再生。当零工经济平台上的骑手们,因算法压榨与系统不公而自发组织抗议,高呼“困在系统里的人”时;当富士康工人以悲壮的“十三连跳”控诉非人化的生产制度时;当全球供应链末端的血汗工厂工人为基本生存权而抗争时——这难道不正是阶级叙事在当代困境中迸发的、不屈的火焰?它从未真正熄灭,只是变换了表达形态。阶级叙事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对剥削与异化现实的回应,是劳动者寻求解放的内在精神驱动。阶级叙事作为无产阶级的底色,其价值远非停留于对过去的诠释。它更是一把锋利的刀,刺穿当下社会“阶层固化”、“新穷人”等现象的表层迷雾,揭示其背后资本逻辑持续运行的冰冷现实。它也是照亮未来的探照灯,为超越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提供方向与动力。在这底色之上,无产阶级得以不断描绘自身的存在图景,校准行动的方向。
阶级底色不会被消费主义的浮华轻易涂抹,不会被后现代的解构话语完全消融,更不会因暂时的沉寂而褪色,它深植于无产阶级的生存处境与解放渴望之中,如地火奔涌,终将找到喷薄而出的裂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阶级斗争的新的开始,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专政,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更要在文化上占领津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毛主席的晚年做出了伟大的成绩和表率。
在私有制复活的当下,更要以阶级叙事为底线,推动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复兴,迎来共产主义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