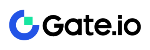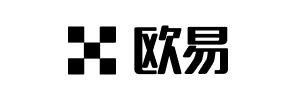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火星报》提出: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给同志们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详细的发挥。
随后列宁撰写的《从何着手?》于1901年5月出版了。
各个委员会都读了《从何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出一个相当的建立组织的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的一种尝试。同时他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和看到,“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在没有相信这个建筑的必要和建筑计划的正确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
如果同志们采纳这个提供他们考虑的计划,那么他们执行这个计划就不是由于“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相信它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如果他们不采纳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草案”就会始终不过是个草案。——难道这不是每个诚恳地对待问题的人都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吗?
事实却是,这个计划草案(《从何着手?》)被经济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责难。 “《火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错误就是它那个全党组织的‘计划’”(波·克里切夫斯基);“《火星报》有轻视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而偏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结果就在第四号上所载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全党的组织计划。”(马尔丁诺夫)。
在《工人事业》杂志上还有一大堆的的攻击,如:“并不是报纸能够建立党的组织,而是相反……”,“一个站在党的上面、不受党的监督、因拥有自己的代办员网而离开党独立存在的报纸……”,“为什么《火星报》居然忘记了它自己所属的那个党内实际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呢?……”,“拥有固定的原则和相应的计划的那些人,同时也就是全党的实际斗争的最高支配者,他们可以命令全党去执行他们的计划……”,“这一计划把我们的生动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组织都赶入阴间,而想把一个幻想性的代办员网呼唤到人世上来……”,“《火星报》的计划如果得到实现。结果就会连我们这个已在形成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痕迹都扫除净尽……”,“一个宣传性的机关报成为全部实际革命斗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我们的党对于强迫它完全服从一个自主的编辑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的态度”等等。
一旦提议成立一个统一的机关报,一旦提议在这个机关报的理论指引下开展革命斗争,就一定会招致诸如此类的责难和攻击。
如果在攻击一个计划草案时不只是“谴责”这个计划并劝同志们拒绝这个计划,甚至唆使那些对革命工作很少有经验的人去攻击计划起草人,而所以实行攻击,又只是因为这些起草人擅敢“立法”,擅敢充当“最高支配者”,即擅敢提出一个计划草案,——难道这不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吗??如果人们对于那种想把地方活动家提高到更广阔的见解、任务、计划等等的水平上来的企图提出反驳,并不只是由于自己认为这种见解不正确,而且还由于有人“想”把我们“提高”一步而感到委屈,——试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能够发展,能够前进吗?
一、《火星报》在提议全俄政治报“计划”前的努力
既然我们迫于目前秘密工作的条件几乎任何一件涉及我们同各个委员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的事实都不能向读者说明,试问我们怎么来回答这种责难呢?难道信口提出一种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责备的人,居然走到我们前面去,这只是因为他们无所顾忌,因为他们根本轻视革命者必须把自己所拥有、所建立或力图建立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联系都仔细地隐蔽起来的责任。
《火星报》在提出上述计划(《从何着手?》)以前,曾经应约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
【《火星报》曾经应约向崩得中央委员会寄去了几篇论文】,《我们的纲领》——内容是直言不讳地声讨伯恩斯坦主义,反对合法刊物及《工人思想报》上所表现的转变;《我们的当前任务》(要“创办一个正常出版而与一切地方团体密切联系的全党机关报”,揭露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的弊病);《迫切的问题》(批判认为在着手出版共同机关报以前必须先发展各个地方团体的工作这种反驳意见;坚决认定“革命组织”有头等重要意义,认为必须“使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这些文章,在革命初期很有必要,而且起到总揽全局的作用】
【《火星报》曾经向预定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实际未召开)起草了一份书面报告(因会议未开,所以未提交,并销毁了)】。在这个报告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目前这个十分混乱的时候,我们单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不仅不能解决统一问题,并且可能会动摇建党这种伟大的思想,因为在目前不守秘密的现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坏;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号召一切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用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员会真正联成一气,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全部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当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培养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时候,各个委员会和党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为中央委员会了。
【此外,《火星报》支持“斗争协会”提议的出版工人丛书的计划,并编写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本小册子,后来出版工人丛书的计划未能实现,这两本小册子却在国外出版了。《火星报》根据崩得中央委员会提议:共同成立一个“著作实验所”。结果,火星派写出了《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小册子。而崩得提议的著作实验所无疾而终。】
【全俄政治报“计划”是在上述活动均未最终实现的情况下,火星派总结提出的。而上述的这些活动都是由当时有影响的,担负党的责任的人们提出的。事情没有成功,火星派接过了这个责任,提出了创办一个非正式的机关报的计划】。
二、应该是怎样的全俄政治机关报
“如果不在各地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那末有办得极好的全俄报纸也没有意思”,这是正确的。但问题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
《火星报》在说明它的“计划”以前,做了一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使它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都能有准备地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利用它们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现在我们更加理解和统一这一点了。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呢?
“我们过去主要是在有知识的工人中间进行工作,而群众差不多只进行了经济斗争”,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它不仅把有知识的工人和“群众”对立了起来,而且,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那么群众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而为了培养出这样的领导者,又只有依靠经常和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实行反抗和斗争的一切企图才能做得到。《火星报》正是把自己的办报“计划”引申为造成“战斗准备”的“计划”,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骚乱、地方自治派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愤”等等。凡是熟悉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地方组织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这里所拟定的这些“生动的政治工作”的任务有许多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一次还没有实行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能这样来“着手”工作,即首先唤起人们想到这一切,唤起人们来归纳和综合所有一切风潮和积极斗争的表现。现在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降低了的条件下,“生动的政治工作”也只能从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着手,而生动的政治鼓动工作又非有经常出版并且能够很好地进行推销的全俄报纸不可。
把《火星报》的“计划”【全俄政治报“计划”】看做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的人,完全不懂得计划的实质,把提出作为目前最适当的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创建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本线索。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公众号、自媒体账号也能承担这个作用,但是需要一个机关报、机关公众号、机关自媒体平台,以便于统一声音,统一行动方向】。
假使一个人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象七十年代的革命家那样“自发地”乱搞“激发性的恐怖”,乱搞“土地恐怖”,乱敲“警钟”等等,那么,即使他极其诚恳地对狭隘性表示愤慨,极其热烈地想把崇拜狭隘性的人们拯救出来,也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的确所有的人都在谈统一的重要性,都在谈“集合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对于究竟应当从何着手和怎样进行这种统一的问题却往往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想必大家都会同意: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城市中的单个的——假定是区的——小组“统一起来”,那就需要有共同的机构,这就是说,不仅要有共同的“联合会”的名称,而且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要按区来分配任务,而且要按全城范围内的各种专门工作来分配任务。每个人都会同意:巨大的秘密机关所要花的“本钱”(当然是指物力和人力两方面而言)不是一个区可以支付得了的,同时,专门家的才能在这样狭小的场所也是无法施展的。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即使是像一个地区这样的场所也显得过分狭窄,而且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已经有过这样显得过分狭窄的情形。
所以,必须,绝对必须而且首先必须扩大这个场所、以经常的共同的工作为基础来建立各个城市间的实际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使他们“好像是坐井观天”,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从什么人那里可以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从事广泛活动的愿望。这种实际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着手建立起来,因为这种报纸将成为唯一经常进行工作,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推动人们沿着所有的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不断前进的全俄的事业。【网络平台、公众号等现代媒体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是一定要要记住,这些新媒体平台都是掌控在资本家手里,他们与官僚资产阶级勾结,最终与革命阶级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因而是不可靠的。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考虑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策略】。

三、全俄政治机关报是如何起作用的
这样的报纸就会立刻指明这个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就会指明在整个全俄工作中,究竟哪些缺点表现得最厉害,什么地方缺乏鼓动工作,什么地方联系不够,在这个总的巨大的机器中有哪些小的轮子是自己这个小组能够加以修理,或者拿更好的轮子加以替换的。现在还没有做过工作而只是在寻找工作来做的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就能不是以一个既不知道先前“工业”的发展情况,又不知道这种工业生产的总的状况的单个小作坊手工业者的身分,而是以一个广泛的事业(它反映着对专制制度举行的总的革命进攻)的参加者的身分来从事工作。每个小轮子修整得越好,从事共同事业的做零碎工作的人数越多,我们的网也就会越密,而不可避免的破坏在我们的总的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越小。
单是推销报纸的工作,就能把实际联系建立起来。现在,各城市之间因革命事业需要而发生联系是极罕见的事情,至少是例外的事情;而到那时候,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一种常见的事情,它自然不仅能保证报纸的推销,并且还能保证(这是更重要得多的)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流。那时候组织工作的规模就会马上扩大许多倍,某一个地方的成功就能经常鼓励在另外一个地方活动的同志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工作,要求利用现成的经验。那时候,地方工作就会比现在丰富而完备得多: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材料,将成为各种职业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工人的精神食粮,将供给我们许多材料和机会来举行关于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谈话和讲演,同时,合法刊物上的种种暗示,社会中种种议论,政府机关“羞羞答答地”公布出来的种种消息,也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来。那时候每一次发动,每一次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评判和讨论,会使大家都不愿意落后于别人而要求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了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考虑改变进攻计划等等。
同时,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引起现在常有的情形,即每一次示威或每一号地方报纸都往往使所有的力量紧张到“最后挣扎的”地步,使所有人都暴露出来。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要查明“根子”就会困难很多,它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查;另一方面,经常的共同的工作能使人们习惯于把每一次进攻的力量与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适应,使得不仅书刊,就是革命工作人员也容易从别地“调遣过来”。
现在这些工作人员往往是完全消耗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面,而那时就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较有才干的鼓动员或组织员从甲处调到乙处。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情,用党的经费作短程的的来往,后来他们就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末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经常销行于全俄各地。这个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那时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经常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的周围,就会有系统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脚手架【列宁在前文中把报纸比做脚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利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往来,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得的总成绩。但是脚手架对于建筑物本身是不需要的,它只存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提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那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罗斯的可耻的、可诅咒的制度。
这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在机关报的运作中,也是必然的事情。】
四、革命家组织在全俄政治机关报的运行中自然产生
我们的“计划策略”是反对立刻号召举行冲击,而主张“正规地围攻敌人的要塞”的,换句话说,是主张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的。《火星报》认为,激发性的恐怖是句空话,至于说什么只是组织中等人和普遍创办地方报纸,这就无异是替经济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其实,现在应当谈的是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一直到真正的——不是纸上的——冲击开始以前,谈这个组织都不算迟。
有系统的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全面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与革命家组织的自觉地破坏力量互相接近和溶为一体的工作。《火星报》那些把全民政治鼓动工作放在自己的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人,是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在全俄各地以全国报纸为中心来掌握组织线索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十三号和第十四号上所记载的那些示威游行,他们也没有错过去。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示威游行,他们切实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一切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示威游行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工作,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它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牵累,又不为敌人的诡计所陷害。
那么我们为什么特别坚决主张围绕着全俄报纸,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因为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使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的迅速变化着的斗争条件,“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善于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敌人的迟钝,在敌人最难料到的地方和时间突然攻其不备”。假使我们不能规定出一种预定要进行很长时期的工作,同时利用这种长期工作的过程,使我们党在任何意外情况下,在事变进程无论怎样加速的情况下,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政治策略和组织计划,那我们就简直会成为可怜的政治冒险主义者。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造全人类的生活条件,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应当因长期工作的问题而“感到不安”。
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日常的平凡的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将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平凡的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转变为平静时期往往是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转变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非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革命本身,也决不能想象为单一的行动,而应当看做是比较激烈的爆发时期和比较沉寂的平静时期的几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和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并且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各方面的生活、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起来的政治鼓动工作。
在现代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是绝对无法进行这种工作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工作人员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事实上,可以看看我们时常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被全部破获的情形。在所有的地方组织缺乏一种共同的经常工作时,这样的破获事件往往使工作间断数月之久。如果所有的组织有一种共同的工作,那末即使遭到最厉害的破获,也只要有两三个坚强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组同总的中央联系起来,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在目前也产生得很迅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获,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央建立联系了。
另一方面,再拿人民的起义来说。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想到起义并且准备起义。到那时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表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的结果。相反,在办理和推销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能够为它在起义时获得胜利提供最大保证的经常性工作。①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意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②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养成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定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③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善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一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有所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回答这些“变故”,——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④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就没有办法来集体讨论起义计划,并且没有办法在起义前夜采取必须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步骤。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在书房里幻想出来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而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五、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阶段
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约十年,大致是1884-1894年。这是社会民主派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思潮的人还寥寥无几。当时社会民主派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1894-1898年。这时社会民主派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了。这是它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知识分子纷纷热中于反民粹派的斗争,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纷纷热中于罢工。大多数领导者都是些很年轻的人。他们因为年轻,在实际工作方面缺乏修养,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但他们的工作规模大都是很广阔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时,是抱着民意党人的那种观点的。他们在少年时代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行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印象,必须进行斗争,必须与那些始终坚持民意主义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在这个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工人运动中去进行工作了,同时他们“一分钟”也没有忘掉启发了他们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
第三个时期(1898-?),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走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增长,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人阶层包括进来,并且扩展到全俄各地,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屈服在广阔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了。社会民主主义被那些出版合法书刊的布伦坦诺派和出版秘密书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这个时期英雄们所干的事情,与其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成其为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掺进去的混合物;“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阔、日益积极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与政治斗争有着分不开的联系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却成了替一种“革命的官样文章”和“民主”的儿戏作辩护的口实。【恍惚之中,我觉得列宁预见了21世纪的我们】。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结束,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进入到了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我们深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深信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深信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