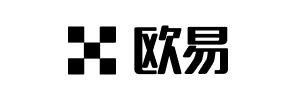经过两天的争论,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8月5日,这个被称为《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的文献在会议上表决通过。这份文献很长,后人们可以从这些很长的文字中反推出很多重要信息,比如:张国焘都对中央政治局提出过哪些责难;而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领导人,又是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张国焘的这些观点进行反驳的;出于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又向张国焘做出了哪些让步……
决议分为七项内容:
㈠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在这一项中,党中央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作出了基本判断:
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国民经济总崩溃的深刻化,全中国的水旱灾荒,农村经济的崩溃与毁灭。国民党反动统治无法而且不能消灭或暂时削弱造成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相反的,他使这些原因更进一步的紧张化了。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1]
还指明苏维埃运动的前途:
红廿五、廿六军及廿九军在川陕甘地区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敌人向我进攻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部队的远离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交通的不便,给养的困难,内部的不统一与冲突,减员、疲劳、冻饿、不满意与失败情绪的增长,财政支付的空前不敷等。而在另一方面,全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发展。尤其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兴奋了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坚强了他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
……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适当的战略战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2]
这段话反驳的是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的怀疑,当然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其局限。
㈡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
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议中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这一战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聚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彻底的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和平创造新苏区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努力与牺牲去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把一切利益服从于革命战争的最高利益,才能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才能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3]
这两段话强调了通过战争创造新苏区的决心,反对了逃避斗争、退却偏安的主张。
——这个批评的指向性不言而喻。
㈢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根本性的原则,中央对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不可动摇。

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4]
这里所指出的“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很显然就是指借中央苏区失利、一方面军减员而质疑中央领导而且急于把“清算政治路线”提上日程的张国焘。
这一项中还特别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正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5]
这也是反驳张国焘质疑遵义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领导正确性的观点,虽然决议也重申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但搁在大敌当前的客观形势和解决当务之急的军事问题的背景下来考量,这样的局限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多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不论在遵义会议或沙窝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那时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所以,决议上才那样写。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考虑和处理,是正确的。”[6]
㈣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
这一项的要旨,是强调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
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7]
决议总结检点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成败得失,特别检点和批评了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包围,击败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
然而这丝毫也不能否认一方面军在一万八千里长征中所给以他的损失。一方面军在脱离中央苏区后这一时期内(十个月)不但在数量上极大的减员(遵义会议前军事领导的错误负最大的责任),即在质量上由于肉体上的疲劳,由于休息时期的缺乏,更由于政治工作的不深入,而受到了相当的损失。这表现在:部队组织的松懈,纪律性的薄弱,游击主义倾向与军阀习气部分生长。在某些干部中发生疲倦、不负责任以及右倾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与思想。这就使部队战斗力相当削弱。不看到一方面军的这些弱点或夸大这些弱点与不去分析这些弱点的来源,必然会产生对于一方面军的过右或过“左”的估计。过“左”的估计可以掩盖目前必须立刻整顿部队,加紧反右倾情绪严紧纪律的实际工作的消极。而过右的估计则可以产生对于一方面军严重的不相信。一方面军的同志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整顿自己的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中央相信,只要取得相当休息整顿的时间与补充扩大,不但可以恢复过去的战斗力,而且可以得到更大的进步。更不要因为目前的相当减员与部分损失而自馁。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该给一方面军经最切实的兄弟的帮助。[8]
同时,决议还表扬了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刻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更不应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运动战方面所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
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与攻击、分裂相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巩固与争取胜利,才能溶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9]
——没有提出更多的批评。
很显然,为了团结,中央在这一点上向张国焘做出了让步。
㈤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
如何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在当时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决议在这一项中阐明了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对少数民族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结合做出了理论探讨。在较为敏感的“西北联邦政府”问题上,决议还是坚持了芦花会议时的观点,但不再指西北联邦政府为错误:
在一、四方面军没有会合以前,四方面军的帮助番民组织游击队,在建立革命政权上,发动番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上得到了相当的成绩。但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是过早的。[10]
一笔带过了“西北联邦政府”的问题。这还是让步。
㈥目前的中心工作
在这一项中,决议综合前述各项的基本精神,重点阐述了当前在两个方面军内部需要加强的工作内容,对两个方面军的纪律特别作出了指示。
大大提高与严紧一方面军的纪律,必须采取严厉办法以保障纪律的执行。同时应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了解红军的纪律主要的不是依靠于强迫,而是依靠于阶级的觉悟。极大发扬党员间及红色指战员间阶级友爱与服从纪律的精神。[11]
对于张国焘特别在意的“组织问题”,决议也在这一项中做出了回答了——
吸收四方面军中党的最好的干部,参加党中央及其他军事政治机关的负责工作。[12]
为了党内和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团结,中央再次在“组织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㈦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路线的斗争
决议在最后部分,极为严肃地提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自两个方面军会师以来的第一次!可见,无论张国焘如何责难,中央在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上,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决议中的最后一项,就是向全党表明中央的基本态度,对违背中央精神的错误倾向,提出不妥协的批判。决议在这一项中指出:
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出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不敢大胆的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以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惧怕少数民族中工作的困难,没有决心在少数民族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于一、四方面军力量的不信任,不了解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伟大意义,甚至根本怀疑到自己部队的战斗力。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碰到某些困难,即表现悲观失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与自暴自弃。这种动摇更表现在对于目前时局的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进到苏维埃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13]
这段话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正是对张国焘表露出的偏安思想进行了批判!
通观整篇沙窝会议决议,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人所处的两难境地,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组织原则,又要顾及党内和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团结,这篇决议的出台,可谓是煞费苦心。而沙窝会议的争论和这篇决议的产生,标志着张国焘与中央在各个方面的分歧与矛盾,在党的决策层内已经完全公开化,坚持原则与维护团结,成为摆在中央领导人面前的又一重大难题。
在“组织问题”上,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委员的11人名单,但也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增补徐向前为中央委员,增补何畏、李先念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样既在部分程度上对张国焘做出了让步,又拒绝了张国焘企图改组中央政治局的要求。会议还决定,任命陈昌浩取代博古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兼任副主任。[14]
随后,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5]
会后,军委纵队也一分为二,红军总部各局除二局外,其余大部分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返回了卓克基、马尔康地区,准备随左路军北上。在此前后,根据军委指示,调整了两个方面军的通信技术人员和器材,将两个方面军的无线电台统一编定序号,编为18个无线电分队(两军共17部电台,其中原属中央红军的12部);统一了电台的组织和通报制度,将四方面军的通报和译电分开,通信和机要分立,促使其无线电技侦工作向专业化方向发展……[16]
8月11日,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奉命率三局、通校、电话队一部进至卓克基,随红军总司令部行动,局长王诤则留在右路军,负责组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右路军的通信联络。[17]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一次得到了“督军会议”的成果,但却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7]《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3]《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7~第6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04~第50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8~第25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5]《中革军委关于周恩来、陈昌浩的任职致各军电(1935年8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6]《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5、第46、48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17]《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革命战争时期》第46~第47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