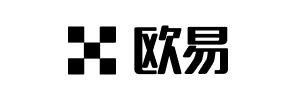矿井关闭后的政治合法性:英格兰前煤矿城镇中的腐败叙事与劳工权力
作者:Sacha Hilhorst 译者:Siant Just
译者按
Amid the workers’ boisterous laughter, the one who had asked me the question didn’t laugh at all. With unwavering seriousness, he pulled me toward the entrance of the main tunnel and gently nudged me along the dim passage for a dozen meters or so. Then he said, “Now you’ve officially been down the mine. Back in the day, when Mao Zedong came to Anyuan to mobilize the workers’ movement, he entered the pit right through here—walked maybe a few dozen meters inside, found a few workers in the tunnel and chatted with them… said the revolution would triumph, and so on…”
Hearing those words, I was taken aback, struck by a sudden and profound stillness.
——于建嵘《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1)本文关注去工业化下英国矿工对政治合法性的态度变化,希望借此讨论社会政治变迁的背景对行动者主体与其结构位置之相互关系的影响。进一步地说,就是通过具体讨论“去工业化”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如何影响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与结果,来描述政治经济制度背景对结构位置与政治行动中介关系的影响;
(2)在文章的目标以外,很难说关于经验事实与分析机制上有所新意,但可取之处在于,提醒我们关注多元主义政治学对“工人阶级专制主义”的狭隘想象与对民主政治议程的保守而无效的规定(李普塞特、亨廷顿之流)。需要继续强调的是,与保守主义的主流“民主理论家”(“美国例外论”和“工人阶级专制主义”是他们最“高雅”的创作)所作的分析相背离的经验事实,一再提醒我们:无需为工人阶级规定它的政治可能性,不管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其提高到想象而非真实的政治高度,或者自由主义理论家通过一再地狭隘预设杀死其政治可能性;
(3)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关注国内的国企研究,一种说法急切地强调其抗争的“非阶级性”,认定即使表现为对耄耋时代政治话语与行动模式的继承也实质是“非阶级行动”,且论据基础便是这种行动与他们所设想的“阶级行动”区别明显。他们将其称为“相对被剥离感”,说这是道义经济学、是“怨恨政治”,而不是真实的“阶级行动”。这一分析一来忽略其阶级话语运用的经验事实(他们认为这只是残留物和习惯),二来又强硬预设失落感、相对剥夺、关怀被撤回的愤怒所支撑的道德话语是“非阶级的”。即使我们承认国企工人因“单位制度”遗产、政治合法性话语和纪律治理,避免明言“阶级”对抗(实际上也远非这回事!!!),但其诉求(对劳动保障、集体福利、体面劳动关系的捍卫)本质上仍深植于生产关系之中,行动又深具特殊性,与农民抗争这一另一重大抗争运动形成显著比较,怎能说完全不具有阶级维度呢?
(4)回到本文,文中“腐败”话语所指向的是国家/政治代表未能履行象征性互惠机制(即劳动换取关怀),而这在中国国企工人中也常以“背叛”、“卸磨杀驴”之类语言出现——它同样构成对其阶级代表性机构和利益结构失序的道德化回应。我们可以下一个模糊、但避免错误的判断:去工业化下的工人抗争处于“伦理政治”与“阶级政治”的结构性交叉。它可能缺乏自觉的阶级话语,但具备阶级性的经验基础与再组织潜能,重要的是不预设其完全背离的图景(但这是困难的);
(5)再进一步地,为何困难?必须意识到现代社会学在识别这些经验范畴上的麻烦之处,不同范畴固然可以建立类型学,一层层分开,但不同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所进行的类型分析就区别很大了,因此必须寻找在经验上加以验证和区别的统一手段;
(6)最最后,即使承诺不预先规定对工人阶级及其政治可能性的一切经验讨论,我仍愿意设想其政治可能性,并在规范的意义上承诺其必然性: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光荣与梦想······
摘要
本文探讨了英格兰前煤矿城镇中政治合法性的逐步丧失。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长期关注煤矿地区的政治特征,这些地区曾以罢工频发和激进的左翼政治立场闻名。近年来,随着去工业化的加剧,这些矿区城镇的政治合法性问题重新引起关注——相较于经济与人口结构相似的地区,这些地方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政治不满与公民冷漠。通过对英格兰曼斯菲尔德这一前煤矿城镇93位居民的访谈与小组讨论,笔者发现,相当多的受访者对当前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持深刻质疑态度,近三分之一的参与者主要通过“腐败”这一叙事框架来理解政治现象。借助近年来有关“腐败言说”作为一种道德化的政治包容与排斥话语的研究,本文提出:所谓“腐败”框架应被理解为一种已然瓦解的象征性经济的反向表达。随着煤矿工人失去了来自政治代表的关怀性回应——这曾是其集体权力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整个政治体系视为腐败的、不具合法性的存在。
关键词:腐败;去工业化;合法性;政治民族志;权力
1
part. 1
引言
在《民主的若干社会要件》这一具有奠基意义的论文中,政治社会学家塞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经典论断(参见 Archer,2010)。但除了这一核心观点之外,李普塞特也对煤矿地区发表了若干重要看法(Lipset, 1959b)。他强调,合法性与民主价值观对民主制度的稳定至关重要。他指出,煤矿城镇由于相对隔绝(参见 Kerr-Siegel 模型,Kerr & Siegel, 1954),往往具有强烈的左翼倾向和激进性,这种特性可能会对民主美德构成威胁。孤立的工人阶级社区中形成的密集而同质的公民网络,可能抑制工人对维系民主制度所需妥协精神的接受意愿。李普塞特进一步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煤矿等行业的就业比例相对或绝对减少,这一趋势对民主而言是有益的。因此,他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推动了“合法性与宽容价值的历史性制度化”(Lipset, 1959b,第98页)。
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再回顾李普塞特的设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煤矿行业的衰落以及前煤矿地区向多元经济结构与更加多样的市民生活转型的进程,并未带来更健康的民主文化。恰恰相反,定量研究发现,与其他经济和人口结构相似的地区相比,这些前煤矿地区呈现出政治信任度低、政治效能感弱以及选民投票率低等特点(Abreu & Jones, 2021)。与其他后工业地区相似,历史上的英格兰煤矿选区在2016年欧盟公投中多数支持“脱欧”,而这一“工业遗产”在统计上被证实是一个显著因素(Langella & Manning, 2016)。学者们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不满的地理分布”(De Ruyter 等,2021;Hendrickson 等,2018),体现出一种以地点为基础的政治断裂(Ford & Jennings, 2020)。在2017年与2019年的英国大选中,许多此类选区成为“红墙”(Red Wall)崩塌的一部分,尽管在2024年选举中它们多数又以显著降低的投票率回流至工党(Curtice, 2024)。随着煤矿产业及其相关制度与基础设施在所谓“去工业化的半衰期”(Linkon, 2018)中逐渐消退,英格兰煤矿区的众多居民日益对现行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提出深刻质疑。
如果前煤矿地区的确存在合法性赤字,那么这一现象是否与其工业遗产有关?又具体是如何关联的?由于去工业化是一个多维过程,交织着经济、社会与情感层面的复杂因素(Emery, 2019;Nettleingham, 2019;Strangleman, 2017),因此很难清晰剥离各个维度,以识别其中具体的机制。尽管学界已对前工业地区的政治转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描述与分析,但地方性的去工业化经历如何具体转化为公民的政治倾向,这一机制仍未被充分揭示。本文通过对曼斯菲尔德镇的政治民族志研究,尝试填补这一空白。曼斯菲尔德常被视为典型的“被抛弃”(left behind)小镇(Goodwin & Heath, 2016;Berry, 2017;另见 Gartzou‐Katsouyanni 等,2018,2021)。基于田野调查(包括与71位本地居民及其代表的正式访谈,以及与另外22位居民的非正式圆桌讨论),笔者发现,相当一部分受访者主要通过“腐败”这一叙事框架来理解政治。“腐败”不仅构成了对当前政治体系合法性的重要质疑,也在面对模糊不清、但极具压迫力的权力结构时,成为人们顺从现实的心理动因之一。

图:曼斯菲尔德镇
“腐败”叙事与该地区历史轨迹之间的联系,仍可在李普塞特所奠定的政治社会学传统框架中理解,即从合法性、经济变迁与地理空间三个维度出发。然而,本文的分析与传统观点几乎完全相反。多元主义学者强调煤矿小镇的隔离性,而近年来的研究则指出,这些地区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联通性。英国矿工之所以能动员并施加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是因为他们控制了煤炭生产与流通中的关键节点。自19世纪末以来,这一结构性优势为他们争取到一系列社会与民主权利(Mitchell, 2009)。尽管并不完美,工会为基层工人提供了参与民主政治的立足点。
煤矿行业的消亡不仅重塑了矿区居民的经济前景,也改变了他们所能享有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资源。去工业化使他们逐渐失去了由劳工运动所争取来的市民福利——体育场被改建为住宅区,工人福利设施被关闭(Emery, 2020),医疗资源也日益紧张。由于这些设施在历史上常被赋予道德意义——作为政治精英对矿工辛勤劳动的“关怀象征”——它们的消失自然也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因此,本文主张,在一个长期以道德化叙事赋予权威合法性的历史背景下,“腐败”这一指控尤具冲击力,因为它正好反转了这一道德逻辑,将政治人物描绘为道德上的弃民。这一过程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变迁相互交织,例如工人阶级选民与工党之间联系的弱化(Evans & Tilley, 2017;Sobolewska & Ford, 2020,第五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政治合法性在前矿区格外脆弱,极易受到质疑。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将首先界定“合法性”概念,并简要梳理与煤矿地区相关的学术争议。随后,文章将呈现对英国曼斯菲尔德居民深度访谈的主题分析结果。在讨论部分,笔者将借助社会学、政治学与批判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将受访者的观点与当地经济变迁相联系,揭示一种机制:即宏观经济结构的演变如何转化为一种独特且高度否定性的政治认知。简言之,那些由产业工人在集体权力基础上争取而来、并以道德化语言加以叙述的社会与政治基础设施(如文体中心、良好的公共空间、与政治代表的紧密联系)在衰退过程中,被越来越多的公民视为“腐败”的象征,从而构成对整个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系统性挑战。
2
part. 2
政治合法性与煤矿地区
在其关于煤矿地区与政治合法性的讨论中,李普塞特(Lipset)提出,民主秩序的稳定性取决于其自我正当化的能力,即其“激发并维系公众对现有政治制度为社会中最为恰当或正当安排的信念”的能力(Lipset, 1959b,第86页)。这一观点建立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合法性的经典论述基础上。韦伯认为,权威或统治(Herrschaft)的长期稳定依赖于其合法性(Sennett, 1993;Weber, 1978)。在短期内,统治者可以通过强制、习惯或物质利益维系统治;但从长期来看,如果统治者无法使其统治获得正当性,则社会秩序将变得根本不稳定(Weber, 1978)。诸如暴力压制或私利驱动等“外在”因素,并不能保障被统治者在长期内的服从,因为人们的动机不仅基于对行为结果的工具性判断,也源自于对行为本身是否正当的价值判断(参见 Marquez, 2016,第21页)。
基于韦伯式定义,本文将“合法性”理解为:即便在缺乏自利动机的情况下,公民愿意接受他人统治的那种信念。这些信念,如近年来的研究指出,是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之上的,取决于公民的规范、期待与感知(Schoon, 2022)。正是这种对“规范与期待”的强调,使合法性有别于诸如政治信任等相关概念(Mckay 等, 2021;Van der Meer, 2017),尽管政治信任确实可以影响合法性的认知。例如,缺乏信任的公民更容易将政治人物的行为视为腐败(Wroe 等, 2013),进而影响其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感受(Erlingsson 等, 2016;Linde & Erlingsson, 2013;Seligson, 2002)。此外,公民与合法性对象之间的关系常常通过诸多制度性中介予以传达(Schoon, 2022)。就煤矿地区而言,工人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激进工会成员身份的影响,这种关系既可能通过赋予工人对制度再生产的参与感而增强其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接受,也可能因替代性政治想象的出现而削弱其合法性认同。
当下有关前工业地区中“非自由主义价值观”盛行的担忧(如 Hochschild, 2024),聚焦于那些被“抛弃”的愤怒选民(参见 Emery, 2023),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上一代学者对煤矿社区倾向于“极端主义”的理解(Lipset, 1959a, b,第96页)。对多元主义学派而言,煤矿社区展现了高度密集、同质化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风险,反映出他们对于容忍与温和价值可能被哪些社会结构所削弱的持续关注。李普塞特借助后被称为“Kerr–Siegel 假说”(Kerr & Siegel, 1954),将矿工的相对隔离视为其激进性的根源:偏远矿村的工人不仅共享工作场所的不满,也分享彼此的社会生活。诚然,英国矿工罢工频率远高于其他行业工人(Church 等, 1991),但将矿区社区一概而论为“封闭同质”忽略了不同煤矿区之间乃至其内部的差异。这种简化催生了多种刻板印象,有的学者将矿工描绘为传统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将其社区视为“正宗”工人文化的遗产;也有学者将其视为反民主倾向的温床(Strangleman, 2018,第20–21页;Arnold, 2024,第288–290页)。
Kerr–Siegel 假说在随后几十年受到多方挑战(Church 等, 1991;Rimlinger, 1959;Scott & Marshall, 2009),其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工人通过对碳能源流动的掌控所争取的权力(Mitchell, 2009)。在依赖煤炭的工业化国家中,矿镇往往位于国家能源体系的关键节点,这不仅使矿工获得了影响社会议程的能力,也赋权于其他能源产业链的节点工人,如铁路、港口和电站工人,使他们得以提出激进的社会与民主诉求(Mitchell, 2009)。孤立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后勤权力”。正如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其福柯式合法性研究中指出的,国家对煤炭的依赖反过来强化了国内民主化的主张(Mitchell, 2011),同时也促成了对外帝国主义的扩张(Mitchell, 2011),如煤炭转向所引发的对全球“加煤站”殖民地的征服(参见 Khalili, 2020)。
至 1990 年代中期,将矿工描绘为富裕劳工或危险激进分子的观点逐渐被关注创伤、社区与失落的新叙述所取代(Arnold, 2024,第290页)。学术界强调,产业遗产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物质结构的消失(Strangleman, 2018),去工业化“仍是当下现实中一个活跃而关键的组成部分”(Linkon, 2018,第2页)。这些“幽灵”、“残影”与“半衰期”如今已成为英国政治的潜在力量,前煤矿区被认为是近年来政治剧变的重要推手。有学者指出,后工业地区之所以“反叛”,是因为它们遭遇了国家层面的忽视与资本撤离(Hudson & Beynon, 2021),被边缘化为“无关紧要之地”(Rodríguez‐Pose, 2018)。这促使学界重新关注(后)工业地区的政治,不再将其不满表述视为强势社会力量的抗争,而是一个衰落阶层的背水一战。
因此,在英格兰后工业地区的政治景观中,权力与合法性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权力与地位的丧失已激起政治上的反弹。这种反弹并不完全源于物质层面的贫困,因为近期的政治不满并未与地方贫困或个体收入形成明确对应关系(Abreu & Jones, 2021;Abreu & Öner, 2020)。相反,关于后工业地区政治的研究强调了“地位丧失”与(相对)衰落所起的作用,并关注诸如痛苦(Silva, 2019)、羞耻(Hochschild, 2024)等情绪,以及地位滑落对工人阶级公民心理所造成的广泛影响(Gest 等, 2018;Gidron & Hall, 2017;Kurer & Staalduinen, 2022)。随着其家乡越来越被边缘化(Olivas Osuna 等, 2021),前工业城市的居民在做出关于公平与代表性的政治判断时,参考的已不仅仅是自身处境,也包括对其所在地方整体境况的感受(参见 Cramer, 2016a),这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怨恨(Cramer, 2016b)。
尽管这些研究视角颇有洞见,但它们较少关注社会—政治制度形态的变迁如何影响结构位置与政治主体性的中介关系。矿工作为关键资源生产者的结构性位置,与各个煤矿区既有的政治文化相互作用,并通过俱乐部、工会、地方工党分支等制度形式表现出来,塑造了独特的社会生活与政治身份。正如“去工业化的半衰期”相关文献所示,这些遗产的消逝或转化并非直线式的过程,而是工业时代的制度结构、话语逻辑与主体认同,与新时代政治经济环境不断交织重构的结果。这一长期制度变迁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转变发生的方式与时机(Pacewicz, 2016a, 2016b)。本文的研究正是试图揭示这一转化机制之一,说明去工业化“半衰期”如何塑造政治不满,并通过民族志的细致描绘,为长期被简化为“典型”或其“对立面”的社区恢复其具体性(参见 Strangleman, 2018)。
3
Part.3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作为一种方法论传统,政治民族志在揭示人们日常政治实践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Baiocchi & Connor, 2008;Benzecry & Baiocchi, 2017;Tilly, 2006)。通过“厚描”(thick description),该方法有助于理解宏观结构性力量如何转化为具体现实,以及政治过程如何在具体场景中得以生成(Baiocchi & Connor, 2008;Tilly, 2006)。本研究所在的子领域方法论选择反映出一种不预设“政治”的野心。在完成一轮广泛的探索性调研之后,笔者主要采用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以捕捉公民对政治关系的叙述方式,并探究这些叙述与认同如何在地方性互动中被建构与协商,且如何受到周边制度环境的塑造。
译者注
厚描(thick description):通过深入分析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与社会脉络,来实现对宏微观政治行为联系的理解
曼斯菲尔德镇在学术与公众舆论中经常被描绘为典型的“被遗忘小镇”(Goodwin & Heath, 2016;Berry, 2017;亦见 Gartzou‐Katsouyanni 等,2018,2021)。在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该选区以 70.9% 的“脱欧”投票率位居全国第十五。2017 年,曼斯菲尔德被保守党攻下,这是工党近百年来首次失去该席位,也因此成为保守党“红墙战略”的重要据点,邻近选区如阿什菲尔德(Ashfield)与博尔索弗(Bolsover)随后亦转投保守党。2024 年大选后,工党再次赢回曼斯菲尔德席位,但投票率下降至仅 55.8%。
正如其他煤矿区所体现的那样(Beynon & Austrin, 1994),当地的政治文化植根于劳工运动所构建的一套密集的工人制度结构(Taylor, 1972),长期以来虽坚定支持工党,却并不总是具备强烈左翼倾向(Gibbon, 1988)。以 1984–1985 年矿工罢工为例,许多诺丁汉郡矿工拒绝响应全国性罢工号召,转而加入新成立的“民主矿工工会”(Union of Democratic Mineworkers)。曼斯菲尔德的矿工普遍认为自己拥有“终身职位”,在诺丁汉郡,极少数矿工坚持罢工至最后(Beynon, 1985;Emery, 2018;Gibbon, 1988;Samuel、Bloomfield 与 Boanas, 1986)。当地国家矿工工会(NUM)的横幅上写着“人数虽少,意志尤坚(so few, so strong)”。这一历史提醒我们:该地区的矿业传统及其政治意义一直存在多重且相互冲突的解读,不能简单视为“工党铁票仓”。
虽然该镇如今常与后工业衰退联系在一起,但其曾以较高收入与繁荣的制造业著称。曼斯菲尔德位于资源丰富的诺丁汉郡北部煤田之上,该地区一度被视为国家煤炭委员会(National Coal Board)的“皇冠明珠”(Emery, 2018)。男性多在城郊多个矿井中工作,女性则主要在商店、办公场所或城内外的纺织厂就业。20 世纪 80 年代末,矿井关闭速度加快,县内最后一座矿井于 2015 年关闭。1990–2000 年代,当 Marks & Spencer 等大型零售商将供应链外包海外后,当地纺织业也随之消亡。在地方政府与开发机构的再开发叙事中,当地居民被描绘为“愿意做繁重、不规律工作且报酬不高的劳动者”(Strangleman 等, 1999)。如今,当地就业以医院、大型超市和养老院为主,薪资普遍偏低;另有部分居民通勤至周边更富裕的城镇工作。由于地理位置处于英格兰中部,该镇现已成为低薪物流与仓储工作的集散地,Sports Direct 与 Amazon 是主要雇主之一(Done‐Johnson, 2021)。
在 COVID-19 疫情高峰期间经历数月间断性访问后,笔者于 2021 年末展开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调查,常驻当地并参与社区活动进行参与式观察。几位本地居民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引路人。在一个对外来者普遍持怀疑态度的地方,这种帮助尤为宝贵。笔者作为一名外来者的身份十分明显,也是一名移民,尽管在英国已生活多年,但受访者常会询问我的口音来源。正因如此,笔者深知自己无法捕捉到所有语境与细节。但“外来者身份”也并非全然不利(Sana 等, 2016),受访者反而表现出极高的坦率,愿意分享一些极其私密的生活经历。
样本在性别与年龄上基本均衡。仅有两位受访者为黑人,这与当地人口结构相符,但也限制了相关分析。移民在样本中略显不足,部分原因在于一些从事不稳定工作的移民担心受访可能带来职场风险。在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上,绝大多数受访者自认为属于工人阶级,许多人来自“矿工家庭”——父亲、叔伯或祖父曾在矿井工作。其中 18 位受访者本人曾是矿工,多集中于小组讨论中,亦有部分人接受了较为正式的深入访谈。除两人仍经营小型企业外,其余皆已退休。仍在就业的受访者从事的职业种类繁多,包括体力劳动(如当地中心公园的清洁工)、低级行政岗位、零售、社会照护,以及在学校、医院或地方政府单位工作。极少数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受访者包括:一位在图书馆系统工作者、一位在大型房产协会任职的高薪职员以及若干本地商人。
我主要的田野区域包括当地足球俱乐部、一家咖啡馆、一家酒馆以及一片社区花园/分租菜地。在被邀请下,我也参与过生日聚会、节庆活动与一次葬礼。
访谈通常在受访者家中或咖啡馆中进行,店主会提供适合访谈的环境。访谈初期以鼓励受访者讲述其人生轨迹为主,包括其个人经历、对家乡的情感以及政治在其生命中的角色(如有)。随着访谈深入,笔者试图理解受访者对政治所持的规范、期待与认知,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形成、受到哪些背景与互动的塑造。他们会提到哪些具体的情境?哪些社会关系或经历塑造了他们的政治感知?他们又是如何在广义的政治场域中行动的?
最终的数据包括:4 个月的田野笔记、71 位正式访谈对象的访谈录音与文字转录、以及与另外 22 位居民进行的小组讨论详细记录。这些正式访谈平均时长约为 90 分钟,小组讨论则不少于 45 分钟(较短的对话内容记入一般性田野笔记)。分析方法采用“溯因式分析策略”(abductive strategy)(Timmermans & Tavory, 2012)。在整个过程中,笔者持续将访谈发现与关于前工业地区政治不满的文献进行对照。在田野调查及随后的分析阶段,笔者持续撰写备忘录,通过迭代式编码与写作过程,不仅寻找支持性证据,也特别注重寻找反例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4
Part.4
对政治的道德化拒斥
受访者在是否愿意实质性参与现行政治体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与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实质性参与、冷漠性疏离以及道德化拒斥(见图 1)。在谈及自身与政治的关系时,有一部分人表现出积极参与的倾向,他们会谈论价值观(Surridge, 2021)、意识形态、党派认同,以及对政治能力与领导力的评价(Clarke 等, 2011),这与政治学文献中对公民政治判断方式的描述相契合。也有一些人则表现出冷漠与疏离,倾向于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对政治体系既不持正面态度,也无明显反感。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完全不看新闻,也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我这一年几乎都在怀孕”,她说,“我只觉得我需要一些正面的东西”。这类态度与尼娜·埃利亚索夫(Nina Eliasoph)对公民生活中冷漠现象的描述一致:他们认为政治是令人不快或无趣的,倾向于远离“充满争议”或“令人厌倦”的政治议题(Eliasoph, 1998)。部分学者认为,工人阶级公民对政治的这种“冷感”反映出阶级已不再是政治动员的核心框架(Manning & Holmes, 2013, 2014)。

表1:政治话语与合法性
第三类受访者则表现出一种道德化的政治拒斥。这一群体表面上与“冷漠型”相似,亦认为政治对其生活缺乏意义,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政治与政治人物作出了严厉的道德评判。许多人明确表示,政客以及整个政治体系本身都是腐败的。他们对“腐败”的使用既具有字面意义,也带有隐喻色彩:一些人指责政治人物牵涉非法金钱交易,诸如“拿回扣”“中饱私囊”或“收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钱”;同时,“腐败”一词也被用来表达一种更广泛的判断,即政客在道德上堕落,政治体系本身也陷入了失能与腐败的状态。因此,“腐败”既意味着对具体违法行为的指控,也体现出对整个代表制度道德衰败的广泛认知。虽然有些参与者在表达政治态度时会在不同话语之间转换,但总体而言,那些将政治视为“腐败”的人,也往往认为整个政治体制已被破坏或正在崩解。腐败指控不仅是对个别政客权威的否定(对许多受访者而言,几乎所有政治人物都在此列),更是对整个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深刻质疑。
本文聚焦的正是这类受访者,在样本中约占三分之一。他们通过“腐败”这一框架理解政治,从而对政治体系作出道德化拒斥。当下腐败被理解为一种道德化论述,聚焦于“滥用受托权力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衰败”,并始终隐含着与某个未腐败的往昔或他处的对比(Doshi & Ranganathan, 2019,第 2–3 页)。腐败的感知与“未被满足的关怀期待”密切相关,也与社会关系的断裂相联系。尽管不少受访者为自己在选举中能够“独立思考”而感到自豪,并常与“盲目投票给工党”的上一代形成对比,但在摆脱上一代的政治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走向了一种普遍性的愤世嫉俗,甚至声称不相信任何政治人物是真诚的。无论其意识形态立场如何、是否有实际政绩,政客在他们眼中都是腐败的,他们被视为非法代表,是体制崩坏滋生的产物。
4.1
“中饱私囊”:叙述腐败
在笔者驻留曼斯菲尔德的第二个月,当地一位引路人介绍我认识了米莉(Millie),她是一位本地护理人员。从政治上讲,米莉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她的父亲曾是矿工,在米莉的记忆中,其政治观点几乎完全围绕着对撒切尔夫人的强烈厌恶展开。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曾被带去参加反对关闭矿井的抗议游行。米莉不仅不信任撒切尔,更不信任所有政治人物,几乎也不信任何新闻媒体。
米莉:我不了解政治,我现在也还是不怎么懂政治,我宁愿不去看。我现在都不看 BBC 了。我不相信他们讲真话。我觉得那是宣传,是用来操纵人心的。
笔者:操纵人心?什么意思?
米莉:让人们按他们的思路去想。我不觉得他们说的大半是真的。总是有隐藏的议程。这得从撒切尔时代说起,当时关于关闭矿井的那些隐藏议程。他们对我们说一些东西,让我们相信,结果其实是在掩盖别的事。我从小就是这么看的,一直到我长大成人。
米莉通常会投票给某个小党的候选人。她觉得政客瞧不起像她这样的普通人。
“我不喜欢工党,也不喜欢保守党,他们一来就说‘你得听我们的’,根本没有给你反抗的余地。”她预期社会将出现更大动荡:“我一直在说,很快就会有骚乱,我说这话已经很久了。而且我觉得这一切(指新冠疫情)其实就是为了把 NHS 私有化,说真的。”
对她而言,政治人物代表着与她自身坚持的诚实、团结与勤劳的价值观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不信工党,我觉得他们是骗子。我也觉得保守党是骗子。而永远就只有这两个选项,对吧。”当被问到政客为什么要撒谎时,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为了钱,永远都是为了钱。钱和贪婪。你要说他们没中饱私囊,我是不会信的。”
米莉这种对政治的理解与她自身在生计上的挣扎和对地方衰退的感受密切相关。她从小就被灌输要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她的祖母 70 岁时去世前一晚还在上夜班,“她总说,‘我一停工就会死’。她还说,‘一退休就死’。结果她还是死了。”米莉成长于以矿井为地貌标志的曼斯菲尔德,不仅景观中有高耸的井架,还有福利机构和体育场所的存在。然而,如今许多煤矿的足球场地被卖掉或改建成住宅,这让她难以接受。
米莉:你懂我的意思吧?那是社区的一部分。
笔者:而那一套社区基础设施……
米莉:被拿走了。你想让孩子们干嘛?他们没法踢足球,没法打曲棍球。我以前是矿工铜管乐队的一员,那时候每个矿都有自己的铜管乐队。我曾在 Welbeck 矿工乐队、Thoresby 矿工乐队里演奏。矿井开始关闭后,乐队的资金也没了。当然,它们现在还有,不要误会我,但已经远不如当年了。我有个邻居也下过矿,他女儿在铜管乐队,他带我入了行。你看,这一切都消失了。以前学校在周六上午会为 11 到 18 岁的孩子开设音乐班,那也没了,“Sure Start”计划也没了。现在一切都变糟了……我孩子根本无法理解,因为他们从没拥有过。但这让我很痛苦,我心里想:那我该怎么办?
在米莉的叙述中,“被拿走的东西”不仅仅是设施或服务,更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纽带、一种公民文化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政治的根本不信任。
在曼斯菲尔德的竞选中,工党高层常将其候选人描绘为“社区捍卫者”(Mansfield and Ashfield Chad, 2017)。但对许多居民而言,这种说法近乎荒谬。“政客只是关心他们自己”,前矿工、现已退休的罗宾(Robin)说,“他们说的不会去做,根本不兑现承诺。他们撒谎,这不应该。”他补充道:“他们赚了上百万吧?”在田野调查时常去的一家酒馆里,其他前矿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们将前任工党议员斥为“废物”,认为他对高薪岗位流失和市中心衰败毫无作为,却非常积极照顾自己的经济利益。过去工党可以依赖曼斯菲尔德居民的忠诚,如今许多人却将工党代表视为自私自利、虚伪奸诈之人,其承诺与道德主张毫无分量。很多人表示:“他们(政客)一个比一个坏。”哪怕是经济理念偏左的公民,也因此对工党产生了疏离。“政客撒谎,”罗宾说,“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说到底,就是看看你会上当不……他们就是在给自己铺后路。”
当笔者向地方议员提及“腐败”之说时,有人称其为“阴谋论”。诚然,受访者有时确实重复了虚假传言、未经证实的本地流言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但这些言说往往又夹杂着一些真实事件,如议员兼职收入、新冠期间的合同丑闻、2009 年议会经费滥用事件等。“腐败”话语也绝不仅限于社会边缘群体。在各类人口群体中,包括年轻人和女性,这种说法都较为普遍。其中一位女性是凯拉(Keira),40 岁,小学教师。2021年底,我们在她位于曼斯菲尔德北部的整洁联排住宅中进行访谈。她成长于一个坚定支持工党的家庭,但随着年龄增长,她越来越质疑父母那一代人对工党的无条件忠诚。她说,她这一代人更愿意独立思考。她上次投票给了保守党,但下次“可能就懒得投了”。
凯拉:我其实挺同情鲍里斯·约翰逊的,你懂吗?他名义上是首相吧?但我一点也不觉得他有决策权。我觉得他只是个喉舌……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谁给了钱,他就照那人的议程说话。现在的一切都感觉是建立在谎言上的。你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不仅是英国的问题,是全球性的。我觉得腐败太严重了。
对她来说,腐败是当今国家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也是她理解自己无力感的框架。她认为政客夸大了新冠疫情的威胁。
“就在社会上层不断变得更富的同时,其余人却越来越难过日子。”
虽然她自己从未亲眼见过腐败实例——“我离权力中心太远,看不到那些事”,她说——但她觉得这是最直接的解释,能说明为何社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她相信,任何剩余的权威都将逐渐瓦解。她对媒体,尤其是 BBC 的不信任极深。
“[我丈夫] 经常说,‘要暴乱了’。你知道,就是那种,‘人们该受够了吧,凯拉?他们肯定快受够了,那些前一秒说了这样,后一秒又那样的事。’但目前为止还没发生。虽然我真的是,我坚信媒体就是在控制你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有可能哪儿已经在暴乱了,只是我们根本听不到了。”
凯拉的怀疑态度比其他人更坚定,但她并不孤立。许多受访者都与她一样,认为整个体系已经腐烂到了根基。“腐败”这一话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道德意味的表达方式,用以诉说他们在政治代表面前的无力与被剥夺感。
4.2
“他们不是为了我们”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我来到一幢整洁的联排别墅,拜访迈克尔(Michael)和他的妻子玛丽(Mary)。迈克尔曾是矿工,在一次矿井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因此他对煤矿行业既怀有美好回忆,也深知其危险。如今,他们已经安享退休生活。尽管两人最近都投票支持了保守党,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大不相同。迈克尔愿意讨论政策与政绩,而玛丽则普遍抱持不信任态度。她过去在多数选举中投给工党,但在 2015 或 2017 年转投保守党,如今则表示自己以后可能不会再去投票了。
玛丽:我想大概都一样吧。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没人……你真的信任政客吗?不会吧?得了吧。我觉得他们连躺在床上都不会躺直。
笔者:你一直以来都这样看政治吗?
玛丽:是啊。因为我总觉得,他们说的只是他们以为我们想听的。而我觉得这很烦人。我觉得这就像他们把我们当傻子。他们以为我们啥也不懂。我觉得他们是在哄我们,这就是我讨厌的地方。我们不是傻子,我们比你们理解得多得多。
笔者:那你觉得政客是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玛丽:钱。我觉得,正如迈克尔说的,一个议员只要干一届,就能拿养老金。太离谱了吧?他们应该是为了我们去做这份工作的,而不是为了那点钱。毕竟他们一半人连会都不来。[转向迈克尔]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再也不想投票了,我懒得理了。
玛丽所说的“他们本该是为我们工作的”,与采访中反复出现的其他抱怨如出一辙:“他们不在乎”“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不是为了我们”。这些言语揭示了受访者对政治人物未能履行其应有的社会与道德角色的深切不满——即政治人物本应展现出无私的公共服务精神,应真正关心选民的生活。然而,正是这种期待的落空,使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失败不仅体现在具体政策成效上,更体现在深层次的道德层面。
尽管迈克尔并未否认玛丽对政客“自私、算计”的评价,但这些道德批评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他对政治的整体看法。他评判政治的依据并非政客的个人品德,而是他们是否“做成了事”。他指出,前任工党议员“也不全是坏的”,因为那些人曾成功推动火车站的重开。但对玛丽来说,这种政绩并不重要,因为在她看来,那位议员的人品本身就已经“有问题”,火车站开不开毫无意义。虽然他们对市中心衰败和家乡边缘化问题感同身受,但政治人物未能扭转局势,对迈克尔而言并不足以否定政治代表制度本身,因为他对政客的道德投入并不像玛丽那样看重。
在理论上,人们对腐败的感知有可能与对整体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判断并存,例如“腐败说”可能只是一种情绪宣泄,或认为腐败被限制在某个可控范围内,被更高效的法治与制度所约束。但在现实中,受访者往往将政客的行为视为整个政治体系道德破产的体现。腐败叙事之所以具有强大吸引力(相比于“无能”或“理念错误”之类的批评),在于它赋予对政治声音丧失与经济衰退的抱怨以系统性解释和道德分量。尽管他们大多仍然支持“民主”这一理念,但对现实中存在的代议制民主体系以及通过该体系掌权的政治人物,这些受访者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与不信任。
5
Part.5
讨论:礼物与义务
“腐败政治对于普通民众如何象征性地表达、想象并批判被剥削、被忽视与经济衰退的经历具有关键作用,而这些表达又常被民粹主义人物所利用。”地理学者萨帕娜·多希(Sapana Doshi)与玛丽妮·兰加纳坦(Malini Ranganathan)如是写道(Doshi & Ranganathan, 2019,第18页)。本研究的访谈记录与田野笔记提供了鲜明证据,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社会与文化公共服务逐渐衰退的愤怒、对政客漠不关心的普遍感知,以及“腐败”这一指控在言说中的普遍性。对玛丽(Mary)这样的受访者而言,政客只为自身金钱利益服务的信念与地方衰退的经历相互嵌套——市中心商铺关闭、酒馆歇业、集市日渐萧条。“那里啥都没有了,真糟透了……一切都没了。”这与米莉(Millie)的抱怨如出一辙:“他们什么都拿走了,你说这讲得通吗?”
社会基础设施的消失以及代表者角色的转变,可以从结构层面理解为煤矿区相对经济衰退与政治代表实践变化的体现(参见 O’Grady, 2019 关于工人阶级代表的消失;Sobolewska & Ford, 2020 关于政党结构的职业化;以及 Lawrence, 2023 关于工党与地方性制度的脱嵌)。但关键在于,这些变化在受访者的叙述中并未被视作可由民主政治加以应对的结构性转变,而是被理解为一种道德上的失败,政客与更广泛的政治体系一并被卷入指责之中。与腐败指控并行的,是对政客“远离社区”“不关心民众”的常见抱怨。
正因腐败话语与人们对“联系”与“关怀”的期望密切交织,因此它并不应被理解为对“清廉”与“程序”的呼吁,而是一种对承认与社群关系的要求。人类学者莎拉·缪尔(Sarah Muir)与阿希尔·古普塔(Akhil Gupta)指出,腐败话语中常含有矛盾愿望:“一方面对法治、程序与正义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渴求超越法律的社交性、裁量权与亲密性”(Muir & Gupta, 2018,第10页)。在受访者的想象中,“腐败政客”的对立面并不是冷冰冰的官僚,而是关心社区、扎根本地、与民众情感相连的公共服务者。他们在描述自己对政治的期待时,常借助一种源自过去的“关怀”与“道义参与”的想象,借此反衬当下的腐败现实。他们对政治表达权的丧失、对社会与文化资源获取的失落,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政治代表的贪婪与道德堕落。
我们可以推测,之所以这种撤除性的现实(公共服务的减少)被从道德视角理解,而非结构视角,正是因为这些服务在历史上本就被赋予了道德话语色彩。例如,历史文献表明,公共澡堂和文体设施的建设是工人运动权力的体现,其增加往往与罢工或罢工威胁相对应(Morgan, 1990)。然而,这些服务逐渐被讲述为道德化乃至宗教化的产物。正如 20 世纪中期一位议员所言,公共澡堂帮助矿工完成“净身仪式”;而矿工社区的社会福利是应得的,“因为没有哪国矿工比英国矿工更勤劳”(《矿工福利法案》,1952 年,Hansard – 英国议会)。另一位议员称:“如果一个人选择在地底深处谋生、生产如此关键的资源,被剥夺了阳光的滋养,那么当他重返地面时,他理应享有最好的设施。”(同上)这些福利被视作“关怀的象征”,是政客表达对矿工群体支持的手段,同时构筑起一个以关怀、社区和辛勤劳动为核心的共享道德想象空间。
若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视角来看,劳动力与社会福利之间的交换是一种被“误识”的过程。这种交换并未被理解为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博弈,而是被想象为某种互惠关系,逐渐构建为一种道德纽带(Bourdieu, 1997;Chanial, 2010;Silber, 2009)。在工业鼎盛时期,曼斯菲尔德这类城市的居民从代表者那里获得了一系列具象化的“礼物”:来自中央财政的慷慨拨款、地方企业在罢工压力下做出的让步,使地方建设得以展开。有民族志学者将这种模式称为“礼物与义务”的制度(Pacewicz, 2016a)。国有化之后,这些福利通常由国家直接提供——民众“赠与”选票,作为交换,他们获得所关心之事的投资(如休闲空间、社区中心);而艰苦的井下劳动则换来煤炭委员会提供的俱乐部、乐团与社会福利。这并非理性经济人的交易,而是一种社会联系,这种交换被转译(euphemised)并误识为一种社会-道德关系,甚至是一种“关怀”。
然而,随着撒切尔时代对地方财政的改革,以及那些能通过罢工施压的产业的消失,曼斯菲尔德居民失去了自身的议价地位,也不再能获得同样的“关怀象征”。2010 年代的紧缩政策进一步削减了这些供给(Dagdeviren 等, 2019;Gray & Barford, 2018),曼斯菲尔德受影响尤为严重。访谈中充斥着体育场改建、社团关闭、医疗服务难以获取的例子。如今的受访者仍以强烈的道德语言讲述政治,他们相信辛勤劳动本应换来某种形式的表达与关照。然而,这些叙述并未增强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反而加剧了对现行代议民主制度与掌权者的谴责,将其描绘为道德上的堕落之人。
正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指出的那样,合法性机制本身常常是权力的软肋,极易被反击(Scott, 1990)。如果统治建立在“关怀”的合法性之上,那么统治者就很容易被指控“漠不关心”。20 世纪长达数十年的“关怀象征”正在逐渐撤除,而“赠与选票”的居民却不再获得相应的回馈。当政治关系被构想为建立在“关怀交换”之上的道德联系时,其反面便是腐败指控——即所有资源只为统治者自己所用。因此,笔者认为,这是地方相对衰退的社会经验如何转化为一种政治倾向的路径之一,尤其是一种与既有合法性话语相冲突的倾向。
当然,也有批评者认为“合法性危机”的说法被夸大了。他们主张,如果真的存在如此严重的合法性缺失,公民行为应当更具对抗性(Marquez, 2016)。确实,大多数受访者在政治上表现出相对被动。他们鲜少参加抗议,与任何政党或运动无关;尽管许多年长者曾是工会成员,但如今仍在参与工会活动的寥寥无几。那么,如果他们真如自己所说,相信政客对他们的死活毫不在意、媒体蓄意撒谎、金权操控议程——为何不采取更激烈的政治行动?
此处,“腐败”话语再次提供了解释路径。当人们感到自己面对的是邪恶而强大的力量,自然难以对抗,抗争的希望也随之减少。腐败话语既是一种对政治合法性的强烈挑战,也是一种保持政治消极与顺从的心理动因。在理论上,服从、宿命论与屈从是彼此有别的,但在实践中,三者的行为表现却往往难以区分,尤其是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常在这些态度之间游移,时而矛盾。但无论如何,“腐败”框架所具有的去合法化力量,都是不容忽视的。
6
Part.6
结论
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指出,在英格兰的前煤矿社区中,政治合法性可能正在部分丧失。多项调查表明,当地居民普遍不信任政治体系,并感到政治上毫无力量。通过民族志方法,本文指出:曼斯菲尔德镇的许多居民已逐渐形成一种信念——现行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深受腐败侵蚀。“腐败”话语在这里作为一种道德性话语运作,用以理解政治排斥与对被授予权力的滥用行为的诊断。许多受访者认为自己已经将选票“托付”给政治人物,而对方却背叛了这种信任——他们未能提供应有的关怀与回应。
本文主张,这种“腐败”感知是去工业化长期效应(或称“半衰期”)转化为特定政治倾向的一种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政治理解方式与当代政治经济现实发生碰撞,激发了对现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深刻怀疑。
本文对合法性的理解也对李普塞特(Lipset)所提出的经典理论提出了修正建议。冷战时期的多元主义政治社会学长期以来影响着我们对今日民粹主义动员的解释框架,而它本身则对政治光谱两端的激进价值均持警惕态度(Jäger, 2017;Stavrakakis & Jäger, 2018)。李普塞特本人在《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上也曾将工会描绘为不民主的组织(Archer, 2010;Lipset, 2010),他怀疑这些组织助长了非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工人阶级的权威主义倾向(Lipset, 1959a;Miller & Riessman, 1961)。但在曼斯菲尔德的案例中,我们却能观察到工会所发挥的民主化力量——它们通过动员集体力量争取更广泛的社会与民主权利。当地的劳工组织体系并未将力量导向反民主的方向,反而通过关怀、社区和劳动等道德话语被转译为社会性供给,这些话语不仅没有削弱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其基础。而今,这些曾经赋予政治代表合法性的道德话语,反过来成为质疑他们合法性的工具。
近年来,一些学者呼吁通过推动反映后工业地区工人阶级生活的文化产出(Hochschild, 2024),以及拓展工人阶级政客进入政治体系的路径(Elsässer & Schäfer, 2022),以回应地位丧失问题。尽管这些观点值得肯定,但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民众已将政治视为根本性腐败的情境下,这些措施远不足以修复政治系统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仅仅选出工人阶级背景的议员,并不能自动恢复人们所怀念的“以社区为本”的情感连接,这一过程还需要重建或新建能够真正让公民实现问责的集体性制度平台。此外,如果不对公共服务、公共空间与休闲设施进行实质性再投资,那么政客也很难说服选民自己真正关心他们及其所处的社区。
本文的分析强调了权力的丧失如何转化为一种特定的政治主体性。像曼斯菲尔德这样的社区虽已失去结构性权力,却仍保有这样一种信念:辛勤劳动理应获得一定形式的关怀与尊重。过去由这种权力带来的公共性支持已经被持续撤除,留下的则是一种广泛的“对腐败的感知”。由于缺乏可供动员的激进政治事业,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侵蚀尚未演变为一场急剧的合法性危机。然而,合法性建构的失败确实使公民更易被各种异质化的社会运动所动员,其中也包括潜在的非自由主义取向的运动。
在最近一轮大选中,曼斯菲尔德约有一半合格选民选择弃权。这种工人阶级弃权模式极有可能持续,甚至进一步加剧——直到某个新兴政治力量能够将当前的反政治能量转化为一股持久的、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根本性挑战。